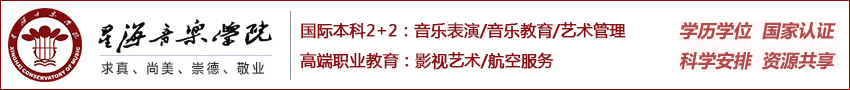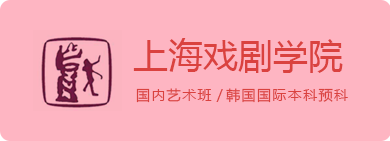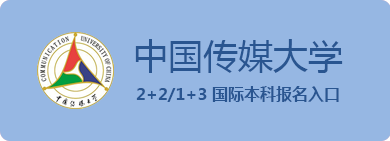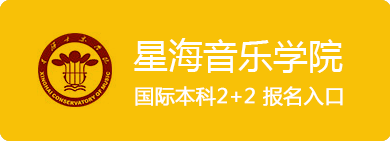播音主持自備稿件:《高處的花朵》
那是具有雪一樣清純的風骨和芍藥一樣柔美姿態的高山之花,看到她的機會并不多,但是一當她嬌羞默默花容不整地展現在你的眼前時,你會禁不住為她的淪落風塵而痛心,為她的香銷玉殞而扼腕嘆息。她的名字就叫——天山雪蓮。
昌吉州地處天山北坡,境內多高山雪嶺,那豐姿綽約的天山雪蓮就常常從雪嶺冰峰上露出芳容,吐露著青春的氣息。然而,我與她第一次相見的時候,場面卻是有些尷尬和令人失落。那是十幾年前的一天上午,我和單位同事一起從呼圖壁縣的南山峽谷中向西天山進發,一路閑游,蜿蜒起伏的山道上,漸漸多了碎石、馬糞、羊糞蛋蛋,一條山間溪水跟著我們唱了一路。云杉、溪水、照進溝口的霞光,還有遠遠的一只鷹盤旋在藍藍的峽谷上空,給人空靈清新之感。
山隨路轉,走進天山溝口沒多遠,我們就需要仰視才能看到遠處銀白的山尖尖了。忽然,我看見在一處狹窄的牧道上,站著一高一矮的兩個哈薩克女孩,仿佛在等待什么人。那個高一點的女孩手里似乎還拿著一個閃著銀光的植物,向我們招搖著。
“叔叔,要雪蓮花嗎?”那女孩子怯怯地問我說。
我低頭一看,果然是一株攔腰折斷的花兒,細長的桿兒,寬大的襯葉,銀白的花冠。不過是采摘下來的時間長一點了,有些萎蔫,失了生動鮮活的光澤,簡直就是一株平庸的野草模樣了。
我湊上去聞聞,清香淡淡;拿在手里掂掂,芳姿柔骨,并不見什么特別傳神的地方。而我是早就在高中時代就借著碧野的《天山景物記》展開對她的幻想和膜拜了。那文中說:“超越天山雪線以上,就可以看見青凜凜的雪的寒光中挺立著一朵朵玉琢似的雪蓮。”
我想,那長在高山之巔、冰雪之側的冷美人,一定是芳香透骨,麗姿銷魂的吧。然而,現代漢語詞典中對她的描述卻很一般,道是:“草本植物,葉子長橢圓形,花深紅色,花瓣薄而狹長。生長在新疆、青海、西藏、云南等地高山中。花可以入藥,有滋補、調經等作用。”
然而,在我看來,散文的唯美和詞典的準確冷靜,似乎都不足以表達出雪蓮的全部神韻和內涵。如今,我看到的雪蓮花并不是什么“深紅色”,也不是“玉琢似的”,倒像是魯迅先生所言:“生命的泥委棄于地,不生喬木,只生野草。”我看到的是沒有了神韻的天山雪蓮,淪落民間的雪蓮,她的身價也不過區區三十幾元,昔日罩在她頭頂的神秘光環驟然散去了。
我為雪蓮不平和哭泣。后來看到的幾條新聞也印證了我的判斷和良心,天山雪蓮到了最危急的時刻,人們不懂得保護這天山的幼苗,雪嶺冰峰上的姊妹群,而把她當成撈錢的工具,一次次尋覓、連根拔起,然后交易,雪蓮哭泣著,花容不整地來到山下,來到藥店的柜臺上,然后又被藥販子攜帶著走南闖北,淪落異鄉,最后像一具枯骨一樣躺進藥罐子,真的就香銷玉殞了。我在許多像樣的大藥房看到過她的影子,那是一些像骨灰盒一樣的包裝物,里面就躺著一株或兩株雪蓮干枯的軀體,失去了生命的紅或白,只有淡淡的藥香,在印證著那句滋補和調經的蓋棺定論。那新聞在呼吁,趕緊保護天山雪蓮吧,這珍貴的物種在天山里已經越來越少了,特別是天山雪峰的上面,人們像搜尋蟲草一樣搜尋雪蓮的身影實在太可怕了。就連一個哈薩克少女的手中都高舉著一株雪蓮花啊,花兒一樣的年紀,經營著慘淡的花。
那一次,我把雪蓮花還給了哈薩克女孩。我沒買,不是因為她不名貴,而是因為我懷疑她的實際價值了。我倒覺得,她活著站在雪山上的時候,其身價更珍貴,名聲更長遠,姿態更豐腴嬌媚。
于是,我倒懷念起故鄉山中的那些迎風擺動的芍藥花兒了,她們紅的、白的花朵在山野中像精靈一般晃動,仿佛是一串小妹妹銀鈴般的笑聲,在我心間回蕩。

 掃碼關注,實時發布,藝考路上與您一起同行
掃碼關注,實時發布,藝考路上與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