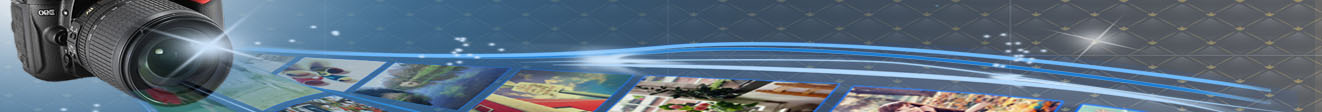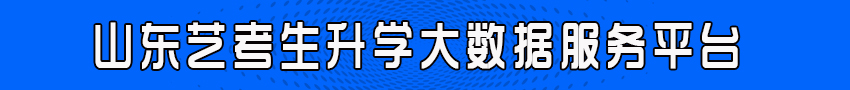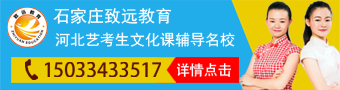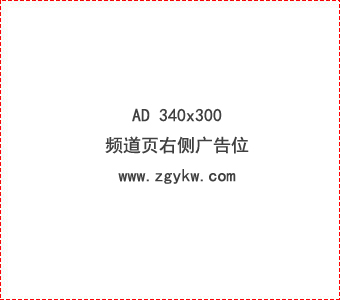曹本冶教授“民族音樂學理論與方法(二)”課程第八篇文章
1968年5月9日-10日我走訪了UCLA的音樂系和人類學系的研究生小組,在南加州大學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社團、人類學系、民族音樂學研究所、非洲研究中心的正式資助下,我應邀就民族音樂學(E)進行了兩個附加討論。在討論中產生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隨之而來的是開放性的思考及友好的爭論。我曾為此專門寫過文章,這篇文章我只就前兩段中忽略的部分進行了改動,并略微調整了句子結構,另外,就聽者與我自己間不同的重要觀點添加些注腳,以便大家更加明確。
演講中的一些觀點源于我所執教的印第安納大學民族音樂學席明納上的討論,因此我要感謝半晌同學們給我的啟發,他們小P、小M、還有Stephen A.Wild\Michael Williams等。
我希望能夠澄清我們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寫這篇文章我并無什么特殊的用意和論點,比如拯救人類學家、民族音樂學家、音樂學家等宏大思慮。save for musicologists, anthropologists, and ethnomusicologists as broad groupings.(雖然這句是讓步,但也可以看出梅利亞姆的胃口)。我的目的是對這些領域(是Musicology、Ethnomusicology、Anthropology嗎?)的一般概括,試著解釋為什么一些學者會專注于特殊的方法?(particular directions指的是什么?)像我一直所做的那樣,我們想彌合表面上的分歧而領導建立起一個真正民族音樂學(E)的學科體系。
沒有人會否認現在E出現了兩個嚴重的分歧。從中我們看到了在E中迥然不同的研究,有的關注于自然歷史過程、有的關注結構技法、有的重描述、有的重分析,當然還有一些什么也不是。我們的所做所為和我們秉承的理念、初衷是多么的不同。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