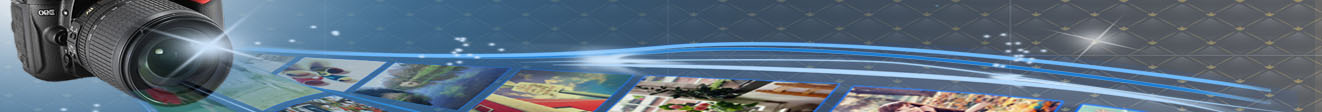音樂的屬性
內容提要:2012年,在中國音樂學院舉辦“中國傳統音樂節”期間,音樂節組委會邀請了美國民族音樂學家提莫西·賴斯(Timothy Rice)教授前來參會,并擔任“太極音樂獎”的評委。期間,賴斯教授在中國音樂學院和中央音樂學院舉辦了系列學術講座,本文便是根據其中的一次講座文本而翻譯的。該文中,主要分析了音樂所具有的各類功能,在英文中用了Resource 一詞,即資源。資源可以是物質性的,成為可以利用的對象;資源也可以是精神性的,不僅可以利用,而且其自身可以自發地產生出某種能量,該文中所闡述的“音樂之資源”便屬于后者。
作者簡介:[美]提莫西·賴斯(1945- ),男,美國民族音樂學家,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
譯 者:張伯瑜,(1958-),男,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民族音樂學是研究人類為什么會有音樂性以及人類如何應用音樂的學科。這個定義將民族音樂學定位于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生物科學之中,專注于在整體人類所具有的生物的、社會的、文化的和藝術的多樣性中來理解人類的本質。
音樂性(“musical”)在這個定義里并不是指音樂的才華和能力,而是指人類創造、表演、有意識地組織、詮釋由其自身所造就的聲音之意義,并在身體和感情上對此意義做出反應的能力。這個定義假設了所有的人類,不僅僅是所謂的音樂家,都具備某種程度的音樂能力,而這種音樂能力(創作和感知音樂的能力)界定我們的人類屬性,提供了人類體驗的標準。音樂思維和行為也許與人類言論的理解能力一樣重要。至少,民族音樂學家可以斷言,我們完整的人性是需要用音樂來體現的。
民族音樂學家相信,我們可以通過我們的音樂性來了解我們的人性,就是說,為了要弄清楚為什么我們的完整的人性是需要用音樂來體現的,我們必須要學習音樂的多樣性。如果想要回答為什么人類是具有音樂性和人類具有怎樣的音樂性這一基本的問題,僅僅研究世界音樂中的一小部分是無法被回答的,所有的音樂都必須完完全全地在它自身的地理和歷史范圍內進行研究。民族音樂學家不會依據想象來判斷“好的音樂”或者“值得研究的音樂”或是“經得住時間考驗的音樂”,并依此判斷來對這些音樂進行研究。相反,他們去尋求,無論何時何地,人們為何熱情地并專注地投入到音樂的創作和聆聽之中,這時候,一些有重要的和有價值的研究便會開始了。
如果我們把民族音樂學界定為研究人類為什么和如何創作音樂的學科,那么音樂的屬性,毫無疑問地成為了民族音樂學家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去思考的問題。
民族音樂學家因其具有基于田野工作的獨特的音樂民族志的優勢,使其已經在理解音樂的屬性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可以說,民族音樂學中的那些最重要的理論,半個多世紀以來其發展一直伴隨著對其的質疑,直到最近,它的姊妹學科——歷史音樂學仍在強調,音樂主要是一種自律的藝術形式,音樂的效果神秘而至高無上,很少或根本不具有社會的現實意義。
從《音樂人類學》一書中阿蘭·梅利亞姆提出的一系列問題中,同時通過借鑒人類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從女權主義和其他社會運動,并從各種哲學傳統中,民族音樂學家已經了解了很多音樂的屬性,在成千上萬的個案研究中這些屬性是作為人類的行為和文化的實踐。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創造了一個豐富的圖景,這個圖景展現了音樂的屬性和音樂對于人類生活的重要意義。
在民族音樂學理論中,關于音樂的屬性問題,或明確、或隱含地采用了隱喻的形式,即”音樂是……”包括:音樂和音樂表演是(1)資源;(2)文化形式;(3)社會行為;(4)文本;(5)符號的系統;(6)藝術。這些隱喻以及另外一些隱喻,可以同時共存,或者順次地分別表現在具體實例中。它們是基于被廣泛討論的社會科學理論、人文科學理論和哲學理論,在以上這些理論的支撐下,音樂的隱喻闡釋了在人類的生活中,音樂意義所具有的豐富內涵。
音樂作為技術或者資源
也許民族音樂學理論中最早關于音樂本質的討論主張去研究音樂在社會和文化中作用以及在個人心理層面中的功能。阿蘭·梅利亞姆稱之為“音樂的功能”。他列出了數不清的方式,傳統社會將音樂用于生活的各個領域,這表明了音樂幾乎與所有的文化活動和社會生活都有著密切的聯系,從出生到死亡,從忙碌的工作到閑暇娛樂。然而,在一種人類學的傳統中工作,即所謂的結構功能主義,梅里亞姆對抽象問題更感興趣,也就是在社會中這些音樂的功能是怎樣發揮作用的,或者用現代術語來說,個人和社會如何將音樂作為技術或者資源,幫助他們達到不同的心理訴求和社會目的。盡管結構功能主義已經不再指導民族音樂學家的思想了,這個“音樂是與人類心理和社會生活功能有關的,它是人類達到某些目的的資源”的概念,仍然深深影響著民族音樂學家對于音樂本質及音樂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的思考。
最簡單地說,音樂是心理或社會的資源,或者說,音樂是調節心理和社會的方法。音樂作為社會資源,顯示出四種基本的功能:它是促進社會一體化的方式;它是改變普遍文化價值觀的方式;它是一種交流的方式;它是一種社會群體向自己或其他群體進行展示的方式。
音樂作為社會資源
梅利亞姆在他最初的音樂功能列表中,提示了音樂表演有助于社會的有效性、持續性、穩定性和統一性。關于此功能的一個更現代的理解方式是把音樂的審美與音樂行為和文化的倫理看作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當人們被傳授音樂時,比方說學習制造好聽的音樂,他們也被灌輸了和塑造了一種成為好人(good people)的方式,使他們在其所處社會中,自身所采用的行為方式非常得體。有時候,這個過程是在歌詞中完成的。比如,一個非洲啟蒙儀式也許包括了指導青年人遵守成人行為準則的歌曲。理查德·沃特曼(Richard Waterman 1914-1971)在關于澳洲Yirkalla原住民的研究中寫到:“一個原住民的一生都圍繞著音樂事件。是這些音樂事件告訴他關于他所處的自然環境和人們運用此環境的方式,教育他應有的世界觀,塑造他的價值觀體系,并強化了他對于原住民身份概念和自身角色的理解。”①
有時候,這些對文化的濡化也出現在音樂表演的結構中。比如說,如果狩獵的成功是依靠獵人間的集體協作的話——這種情況經常出現在森林部落,即所謂的中非洲俾格米人之中,他們之間相互協作的、緊密聯系的、多聲部的歌唱就會出現在狩獵之前、之中和之后,并以此來對他們的狩獵起到幫助作用。②學校歌曲和愛國歌曲可以使個體感覺到與社會群體是聯系在一起的,使得個人在競賽和戰爭中支持該群體和該群體的價值觀。群體的表演,無論是大的合唱隊,大的樂隊,或者步調一致的舞蹈者們,都能起到堅實社會的作用,為某一社會群體提供了一種在和諧的社會中檢驗自身行為的方法,同時,用在一種令人滿足的、熱情的和愉悅的綜合方式中來體驗著自己。
音樂還可以作為挑戰有權利的社會制度的資源,因其社會制度在體制上有缺陷,由此而組建以前從沒有過的社會,來激起一個社會群體在基本的文化態度和社會建構上的革命。例如,在保加利亞共產主義時期的后幾年,羅馬尼亞音樂家中那些極端的即興藝術愛好者,通過演奏現代樂器來反對古板的音樂形式,這些音樂形式是由政府支持的民間合奏形式,使用傳統樂器。這對于那些反對集權主義政府的人來說,對于那些在尊重穆斯林少數民族問題上反對政府所主張的極為嚴苛的政策的人來說成為了一種有利的武器。
音樂還可以作為社交的資源,用于那些人們慶祝人生不同階段或者季節輪回的音樂活動中。在這些情況下,音樂促進了社會成員之間的交流,讓所有人了解一個人在人生不同階段的演化,或者相互間交流對于一個季節的共同經歷,如對于炎熱和寒冷的感知以及在這個典型季節里的勞動和社會行為。比如說,生活在亞馬遜盆地的蘇亞印第安人,每一個典禮的音樂表演,都會告訴蘇亞人關于表演者和所表演的季節的一些信息。③蘇亞人的一年可以分為旱季和雨季,但是這些季節不是根據天氣的變化而確立,而是根據所表演儀式的變化和所演唱歌曲的變化。這不僅僅是將要下雨的問題,而是通過演唱雨季的歌曲來告知某個人,或所有人,雨季已經開始了。
歌唱也溝通了同齡人之間的想法:兒童、青年、成人、還有老人。一個年輕男孩可能會歌唱成人的歌曲來傳遞自身成長的信號。一個老年人可能會唱不太有力的歌來標識自己進入了老齡。
還有一種交流的方式,世界上幾乎任何地方的人好像都相信歌唱比起平淡的演講來說能更好地和上帝、祖先和靈魂交流。通常,在典禮的祈禱和禮拜的時刻都會伴隨著特殊的歌曲或者器樂演奏,暗示著那種音樂具有使典禮奏效的特殊力量。在另外的場合中,音樂是用于聯系超自然世界的途徑,是超自然世界在自然世界的信號。非洲的和起源于非洲的靈魂附體的儀式提供了一些最為鮮明的例子。在海地的沃頓(Vodoun)、巴西的坎東布雷(Candomble)以及古巴的薩泰里阿(Santeria)等宗教傳統中,供奉眾神的萬神廟被不同的信奉者通過舞蹈、服裝、打擊樂節奏和歌曲等不同的形式來朝拜。這些傳統中的音樂包括了打擊樂的組合,這些組合由技藝高超的鼓手帶領,演奏出相互交織的、具有復聲性的節奏模式。當首席鼓手感覺到某個訓練有素的崇拜者已進入狂喜狀態,他就會演奏特殊的節奏型,來幫助神靈進入到這個著迷者的思想和身體之中。④
當一個社會群體被忽略,比如當他們被更加有權利的階層壓制時,音樂經常能夠給這個受壓抑的群體成員提供一種強烈的、發自內心的交流方式,使他們能夠與其他群體談及他們的感情、信仰和他們的存在。當然,其他群體成員也可以為他們做同樣的事情。權利階層可以用音樂來控制社會,來迫使少數人群和無權者實實在在地或象征性地被邊緣化。音樂是一種常規的鑒定社會群體的方式,亞馬遜社會的一部分、王室的血統、現代社會的政治黨派、或者社會各不同階層,諸如年輕人和成年人、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窮人,這些都包含其中。在此情況下,音樂具有人們向自身社群成員或群體外成員來展示社會階層的符號認證之功能。在流行音樂傳統中,如朋克和死亡金屬音樂,音樂家和粉絲們保持著對于特殊審美觀念的忠誠,其中包括服飾和音樂風格,這提供給他們一種身份認同的方法,展示其與其他人是不同的,闡明了誰是或誰不是那個次文化的所屬成員。
音樂作為心理的資源
梅利亞姆提出了三種音樂有可能成為心理資源的方式:娛樂、審美享受和情感表達。毫無疑問,在所有娛樂方式中,包括說唱、舞蹈、戲劇、電影、電視和電子游戲等,音樂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情況下,比如在舞蹈中,音樂能夠制造出娛樂的氣氛;再比如,講故事經常會伴隨著音樂,因為音樂可以加強故事的感染力。電影音樂提供了許多實例來展示已經定性化的音樂手段,用這樣的手段可以去強化、甚至去創造浪漫的情調、恐怖的氣氛、期待的心情和歡笑的場景。除了將音樂與其他的娛樂形式相關聯之外,在許多文化中,音樂還可作為消遣手段,作為釋放工作和日常生活壓力的手段以及作為社會關系的潤滑劑。在當今社會中,音樂娛樂經常由音樂唱片來承擔(無線電廣播、電視、CD、mp3等),這些是由專業音樂家制作的,可以用耳機或在家里聆聽。
審美享受,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娛樂形式,這種娛樂形式好像只有當人們融入到音樂表演的時候才可發生,通過一種特殊的形式,如一場音樂會或者一張唱片,把該形式作為一種凝視的對象。不同于從無聊的事物、工作、環境中的噪聲等方面產生的娛樂性消遣,在音樂會上,所有的帶有刺激性的因素都有意地被排除在外,以便能夠專心致志地享受音樂體驗。
幾乎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音樂表演均可作為一種控制情感表達和喚起情緒的重要資源。這種音樂情感表達中所具有的控制力是與憤怒、悲哀、歡樂情緒的自然爆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比如,我采訪過的一個保加利亞的婦女,她回憶了過去的一件事。在她做新娘時,她覺得與她和丈夫一起生活的婆婆對她很不太好,她說著、說著,快要哭了。這時候,有人勸道,“別哭,唱首歌吧!”還真靈,她從不能控制的、令人不好意思的哭泣,變成了可以控制的、體面的唱歌。歌唱不僅表達了個人的情感,也表達集體的情感。歌唱經常會有宣泄情緒的功能,是宣泄不滿和釋放壓力的途徑。不論是個人問題,還是弱勢群體的集體不滿情緒;或是看上去不太恰當的情感表達,甚至是在日常口頭交流上所具有的禁忌,都可通過音樂表達出來。
音樂作為連接心理和社會的資源
音樂作為連接個人與社會的資源是通過以下兩個途徑:肢體反應和文化中的力量。音樂是節奏化的,就是說,它存在于時間之中,通常有一個穩定的節拍和律動,它使得聽到這些節拍和律動的人產生肢體反應,人們會伴隨著拍子擊打手指,用腳打拍子,點頭,走路,行軍和舞蹈。這些普遍的反應提供了一種使一個群體能夠聯系在一起的方式,像一個社會整體一樣來理解和體驗著自己。某些情況下,是為了完成某些具體任務,比如作為統一高效和強大的力量去參加戰爭,或者為了高效率的集體工作。伴隨著音樂的節奏而一起行動,人們把音樂作為從個體的心理反應變了一種社會的資源,這種資源把集體、關系密切的群體以及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整體。
今天的民族音樂學家也同樣理解個體也是制定和挑戰社會規范的動力,而且他們在這一過程中也用音樂作為資源。在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實用理論的影響下,他們已經明白了音樂作為非語義的實踐,可以超出語義的范圍,創造出具有性別化的個體以及一些由社會建構出的身份認同與主體性。⑤例如一項關于尼日利亞以巴旦地區的約魯巴(Yoruba)巨究(jùjú)音樂家和樂隊領隊達友(Dayo)的研究展示了達友如何協調自己和兩個群體之間的關系:一個是他的樂隊為其演奏的上層社會,另一個是他建立的、同時也在利用著的下層社會群體“樂隊男孩”。⑥作為一個半文盲音樂家,他的社會身份很低,是個貧困的音樂家,與他一起工作的也是一些社會地位低下的人,他必須培養這些人的忠誠以便能夠使該樂隊能夠捆綁在一起。因為有錢的富人們會以雇傭最好的音樂家來展示他們的優越感,達友作為一個成功的樂隊領隊,已經可以把自己的地位提升到這樣的人,而且在金錢、聲望和榮譽等方面近乎與他的雇主相同。達友的音樂實踐使他可以構建一種自我認同,那種可以馬上使他成為接近于那些聽他演奏的有錢人的社會群體的認同,同時在社會層面他又不與樂隊成員們離開太遠,以便這些成員不離開他,去到其他地方去追尋更好的人生。他用音樂作為了自我建構的資源。
給出如此短的人類應用音樂的演奏作為到達某種目的的資源的清單,民族音樂學家們有時候試圖去表明,音樂對于人的個體和人類的群體來說是與講演和語言同樣重要的。我們所研究的人群中許多人也支持我們的這種觀點。如同梅里亞姆所說,有一次,在新墨西哥的普韋布洛印第安人告訴人類學家雷斯利·懷特(Leslie White 1900-1975)說:“我的朋友,在沒有歌曲的情況下你不能做任何事情”。⑦
音樂作為一種文化形式和社會行為
關于音樂屬性還有另外兩種隱喻,一是文化形式,另一是文化行為,這兩種屬性可能代表著其文化形式和文化行為,或是與其他文化形式或文化行為相一致。這個觀點源于法國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斯圖爾斯(Claude Levi Strauss 1908-2009)的結構主義理論。在此方面的早期研究之一是有關爪哇島加美蘭音樂的時間組織形式。爪哇島的加美蘭樂隊,西方之外的最大的樂隊,包括了一系列定調的銅制樂器,涵蓋了多個八度,從極低的音區直到在金屬片上奏出的高音。加美蘭音樂家創造出了復雜的多聲部織體。中音區的金屬片狀樂器演奏偶數拍的旋律;較高音區的金屬片狀樂器和定音鑼將旋律的節拍一分為二,或一分為四,對旋律進行裝飾;低音鑼提供伴奏,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伴奏可以被理解為對旋律進行簡化,其結果是一種復合性的節奏,在不同的速度下同時循環進行。爪哇加美蘭音樂的多重時間循環與加美蘭人關于時間的概念相印證,相一致,他們的時間概念也是多重循環的。這個概念依據了當地的不同天數的星期計算體系。這種音樂與文化的一致性導致了一種認識,即這些形式是“自然的”,盡管它們是以文化來建構。⑧
20世紀60年代,阿蘭·洛馬克斯(Alam Lomax)試圖通過一項被標記為“歌唱測定”(cantometrics)的龐大的比較性研究項目來解釋音樂可以作為社會行為的比喻。“歌唱測定”是他創造出來的一個術語,以表示歌曲是“文化的尺度”。他試圖在世界的范圍內來證明歌曲表演的結構是與廣泛的社會結構的展示相關聯的。他聲稱“在任何一種文化或次文化環境內,歌唱是一個行為的標準形式”,這些音樂的方式與文化中的社會組織是一致的。⑨“某文化中受喜愛的歌曲風格反映著并強化著某種行為,而該行為無論對于歌曲風格的延傳,還是對于該歌曲風格在社會建構中的中心性和控制力來說都是很重要的。”⑩
他借用了一些人類學家和其他學科的方法,采用數據收集的方式,從世界上400多種文化中抽取樣本,每種文化選用十首歌曲。然后他創建了一個評估表格,用來對每一首歌曲進行包含36種音樂風格變量的描述,這些變量包括旋律形態、音量、“音質、裝飾、協同程度、節奏和樂隊及合唱的音樂組織形式、表演中的社會組織模式和文本的處理情況”。運用分析數據,他提出了許多基于跨文化視角的、關于歌曲結構和社會結構關系的論斷。舉一個例子,“如果社會包含許多階層,級進音程就會出現得很頻繁。對此的解釋可以是,在一個強調人的高低身份的情境中,相互間的界限就會被強化,所以,你來我往的反應就會非常小心,采用很小的步伐。”此項研究是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當時的民族音樂學家正朝向對某具體文化進行深入的研究,而不是這種廣泛性的和比較性的研究,他們對于洛馬克斯試圖創建一個在音樂理解上的世界性的普適理論和將音樂與社會相聯系的觀點的反映是負面的。他們對其方法論提出質疑,用他們熟知的某些文化之中的例子來說明在同一文化之中音樂風格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以及用這樣的例子來反對洛馬克斯所主張的在同一文化中只有一種主導風格的總結,同時還找出了與洛馬克斯的材料相反的例子來證明其數據統計的方法不能令人信服。盡管如此,洛馬克斯在結論中說道:“在表達和交流的過程以及社會結構和文化形態之間的關系上,這是第一次將可以預言的和具有廣普意義的關系建立了起來”。
盡管今天的民族音樂學家也許不同意這些關系是可以預見的,但是民族音樂學家看上去似乎相信音樂是一種社會行為,音樂與其他社會行為在結構上的同質關系可以通過仔細的民族志研究顯示出來。北印度古典音樂的表演結構也許與演奏者的等級化的社會制度是同質的,或被這種社會結構來解釋的。(11)在這個傳統中,旋律的獨奏者,演奏一種叫做西塔爾(sitar)或薩羅德(sarod)的長頸琉特琴,這些獨奏者相對于塔布拉鼓的演奏者來說是來自于較高的社會階層。這種社會差別轉化到音樂結構中,旋律的即興演奏是主導,鼓手則處于伴奏地位;旋律獨奏者掌握著音樂會,控制著任何的表演結構,并且比鼓手賺錢更多。
在秘魯安第斯山居住的艾馬拉印第安人中,音樂家集體創作出新的作品,這是一種與它們集體性的文化氣質相一致的實踐。(12)這個實例中,政治領導者和音樂領導者必須經常在一種相對平等的集體環境下一起演練,任何人均包含其中,并且回避著沖突。在音樂中,盡管某個人成為公認的“領導”和音樂的以及樂器的制作方面的專家,然而,為即將舉行的宗教節日所演奏的樂曲也是由音樂愛好者(音樂大師們)中的某些重要成員組成的小組集體創作的,由排簫合奏演奏。此曲的演奏程序是由某些人首先試著為作品創作出一個短小的動機,而作品最后成為AA BB CC的結構。
這些最初的集思廣益的樂句常常會比較長。如果人們對一個材料不感興趣,他們就忽視它,而不是直接地拒絕它,就像他們對待(城市)聽證會上的不恰當的主張所采取的態度一樣。在這個時間段,如果一個音樂家對他演奏的旋律或者主題沒得到任何反映,他會放棄它們,然后創作其他的旋律片斷或者保持沉默。然而當一個主張被發現可行,其他人會逐漸地注意它,停止他們自己正在創作中的旋律,然后慢慢地把他們演奏的樂器加入進來,直到每個人都能演奏此旋律。
在這種情形下的音樂作品,很清楚,是一個社會行為形式,它表現出了與政治決定相同的方式。基于這個例子,將西方古典音樂也理解為一種社會行為是不難達到的,西方古典音樂的社會行為在整體文化環境下與個人主義、才能和英雄塑造的觀念密不可分。
音樂作為文本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以上這種結構主義分析最繁盛的時代。盡管民族音樂學家繼續將音樂視為社會行為和文化形式,他們對于同源性和相關性的研究被后結構主義傾向所截斷。后結構主義排斥在音樂、文化結構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靜態相關性,他們更喜歡通過音樂表演,研究社會文化意義中的動態音樂產物。換句話說,這是一個進步,從音樂“反應”文化的觀點轉向了音樂可以生產文化。在格爾茲(Clifford Geertz 1926-2996)的解釋人類學和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的現象解釋學影響之下,這一流派的民族音樂學家把音樂的意義和音樂表演作為文本來解釋和解讀。這種解釋方式是盡可能多地把焦點放在特殊行為的文化動因、意義和系統寓意上來進行解釋。
關于把音樂視為文本隱喻的最早和最清楚的例子是一項關于美國音樂學院中音樂生活的研究。(13)研究者將學生獨奏音樂會,一種典型的獲得學分的方式,解釋為一種展現美國個人主義的提喻,一種儀式化的表演,用以證明學生的專業潛力,或者曝露他們沒有表演天賦,還不具備專業音樂家的素質。這種把焦點放在個人才能和專業生涯潛能的評估上的思維方法是“文化系統”的一部分,其中在才能和潛能上的認知是如此的普遍,幾乎具有了神圣的性質;這樣,便使得獨奏音樂會儀式化了,具有了信仰和價值表達方式的本質。“一場獨奏音樂會是個人祭祀中的一種儀式……在這樣的祭祀中,音樂會作為儀式的繼續,其連續性的功效要求一些人,但不是全部人,能夠獲得成功。”這樣的儀式需要給予生活一種能夠認可個體性的文化系統,“個體主義的文化價值不是……空無的,而是通過儀式行為產生和重復產生而出的”,獨奏音樂會是這種文化系統中許多這樣儀式中的一個。因為這樣的研究是處在所謂的我們自己的文化之中的,所以,很容易理解這樣的解讀方法與演員們自身來解讀自己的行為是不一樣的。然而,這樣的解釋沒有對所要研究的文化系統的深刻理解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能夠形成這樣有信心的理解的關鍵是通過田野工作,在文化之中的長時間浸泡。
音樂作為符號體系
民族音樂學關于音樂意義的研究與歷史音樂學和音樂理論領域的思想直到最近仍在爭論。這些領域的學者們對音樂與語言之間的區別念念不忘,但是在語言中,講英語的人對像“樹”這樣的單詞的含義有著極大的認識上的一致性,而對于音樂的含義,即便是在很小的程度上也沒有這樣的認同,這樣便導致他們得出結論:音樂沒有含義,或者至少沒有共享的含義值得去討論。民族音樂學家們知道,即使我們在音樂中永遠找不到與“樹”相同的概念,但是我們能夠觀察,人類經常像賦予另一些文化形式,如衣服、食物和肢體語言以某種含義那樣來賦予音樂特點和音樂表演以意義,這些含義經常是從不同的歷史和社會的定位來賦予的,所以不同的群體、不同的個體或者不同的時間其意義也不同。
這些有關音樂含義的不同觀點中所包含的問題被佩斯(C.S.Peirce)的“符號學”研究所闡明。佩斯區分了三種形式的符號:象征符號(symbols)、標識符號(indexes)和圖像符號(icons),每一種依據不同的邏輯來運作。語言使用象征符號,這些符號,“是通過語言的定義來和它們的客體相關聯”。象征符號“對于在某種程度上可預知的交流來說具有最大的潛力”,是音樂分析和音樂學解釋的基礎。然而,托馬斯·圖瑞諾(Thomas Turino)卻認為符號使我們遠離了直接的音樂體驗。符號不是音樂含義的核心,它們無法解釋人們為什么能發現音樂具有如此的含義和如此的動人。(14)他指出,標識符號和圖像符號作為不同類別的圖形,它們在一種直接的或無中介的方式中對音樂體驗進行解碼。
一個標識符號是一個圖形,指向一個客體,當與一首特殊的作品或實踐相連時,或者與其他的事件同時發生時,它便在音樂中出現。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一首國歌,具有愛國的內容,在政治場合演奏。很快這首國歌便成為了共享的愛國主義的象征,每當它響起時,就會引起愛國的情感,比如運動會比賽前,甚至當它只是由器樂演奏,而無歌詞時。這樣的例子表明通過共享的集體和個人的體驗而產生的共享性的音樂意義的可能性。正如個人的或個體的標識符號對于音樂體驗是很重要的,“我們的歌曲”現象作為一個經典的案例,是一首被兩個相愛的人分享的歌,一首“標識符號”的歌,即便愛已不在,激情已冷卻,此歌仍然能夠產生很強烈的感情。
圖像符號是一種圖形,在某些方面與其所代表的事物有某些相似性。宗教的圖像符號或宗教繪畫,把一個三維空間的人用二維的平面來表現,可稱之為宗教化的圖像符號或繪畫。常見的音樂圖像符號包括用笛子來模仿鳥的歌唱,用上升曲調表現快樂或者升入快樂的世界,用下降曲調表現墜入地獄,如果用夸張的即興來代表一種圖像符號,表示個人的自由或個人戰勝整個系統的勝利。如圖瑞諾所強調的,對音樂圖像符號的解釋有時候依靠于聽覺的體驗;但是,有些時候,如當人們聽到以前曾經聽到過的熟悉的曲調時,如果把該曲調當作一種圖像符號,它使聽眾感覺到自己是制造該音樂的社會群體中的一員,一種有助于個人認同感的想象行為,而且引發出對此認同感的強烈的感情。當標識符號(indexes)直接與個人體驗和現實“直接相連接時”,“圖像符號(icons)便給我們打開了可能性與想象力的空間”。
圖瑞諾得出的結論是,音樂“包含著直接情感和體驗的圖形”。(15)音樂可以像語言那樣解釋出含義,但是,它終將是一種不同于語言圖形的音樂圖形體系。音樂除了具有創造性意義之外,對人類還有另外的一些重要意義。
當人們采用象征性的符號化思維來思考問題和采用象征性的符號化方式(如同在使用語言時的情況)來進行深刻的感情和體驗的交流,這時候,感情和真實的體驗便消失了,我們無法被滿足。這是因為我們轉移到了更高層次的媒介,一種廣義的交談模式,離開了直接情感和體驗的圖形。“象征符號”……達不到情感和體驗的世界,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音樂之原因。
另一個使得音樂有如此豐富的潛在含義的因素是音樂作為一種符號,其在本質上所具有的復雜性。音樂作為符號具有很多元素,每一種元素可以作為一個圖像符號或標識符號均帶有不同的含義,這些含義之間或相互支持,或相互抵觸。音樂的元素包括旋律、節拍、節奏、樂器音色、聲部、速度,多個旋律或節奏相互交織,構成不同織體和和聲等等。一種現代保加利亞的后社會主義的音樂種類叫作“流行化民間音樂”(popfolk),它使用不同的音樂元素,構建一種復雜的符號,用來標明對想象中的認同感的追求。合成器、架子鼓和電吉他產生了擴音化的音響背景,成為一種全球流行音樂的現代形式的圖像(外象)符號。在音樂符號中,這個元素使得該音樂品種的保加利亞音樂愛好者們將自己視為一種現代人,一種能與世界文化接軌的人,因為在世界文化中這種音樂無處不在。歌詞是保加利亞語,有時會加入風笛等保加利亞傳統樂器,強調了該音樂品種中的保加利亞元素,以便與保加利亞國民性的身份認同建立一種聯系。該音樂的一些最好的音樂家和歌手都是諾瑪人(Roma),所以這種音樂特別強調單簧管和薩克斯的獨奏,用自由性的節拍和節奏符號化地體現出了諾瑪的和土耳其的音樂風格與音樂類別,有助于創造出一種認同感,認可甚至慶祝保加利亞的奧斯曼帝國的歷史以及保加利亞與泛歐洲化世界的不同。該音樂品種中的這些交錯的和具有沖突性的音樂標識符號(indexes)引起了非常不同的情感反應,有助于解釋為什么音樂是音樂含義的和音樂情感的如此有力的承擔者。
音樂作為藝術
盡管民族音樂學家已經花費了大部分時間去研究一種隱喻,用來替換音樂是一種藝術這一概念,其結果是音樂作為藝術的內涵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宣稱音樂是一種藝術,打開了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也就是,什么是藝術。簡單地說,關于藝術的定義,存在著兩個極端。
一種極端是西方的藝術觀念。在藝術史的大部分歷程中,此觀念把藝術看作是一種制作技巧,它是與熟練地掌握一種工藝,如繪畫、家具制作,或者音樂演奏是同義的;或者與一些實踐活動,如戰爭的藝術或者醫學的藝術也是同義的。
這個定義把其著眼點主要放在了藝術的工作者上。即使是從18世紀以來,西方哲學的發展大大改變了這個陳舊的定義,它仍然是民族音樂學家所接受的理論,因為它強調了藝術的制作和人文的力量。這個定義回避了純專業藝術和功能性藝術的區別,在一定程度上適合民族音樂學家的世界觀。在此定義下的藝術存在于地球上的每種文化之中,很多不同文化的民族音樂學研究都被那些令人著迷的有關音樂技術和工藝的材料所填充,音樂技術與工藝用另外的詞匯來表示便是音樂藝術。
另一個極端是把藝術的定義聚焦在藝術的能力和“藝術工作”上,用來表達情感(就像音樂常常具有的功能),表現和模仿與此工作不同的事物(如同繪畫和雕塑常常顯示出的特點),顯示著形式上的元素,這些元素能夠引起人們的興趣并值得為了這些形式而去關注它們(梅利亞姆的“音樂聽上去是它自己”),而且能夠產生感性體驗,這些體驗能夠通過審美來判斷,即可以是美的(或丑的)、有意味的,等等。
這樣的判斷是基于來自藝術工作自身的真實質能,如優雅、平衡、復雜、等類似的質能。前面關于隱喻的討論已經闡述清楚,民族音樂學家在廣泛且不同的音樂文化中找到了大量證據,這些證據作為一種資源可以用來表達情感,也可作為一種符號系統中的文本,用來展現音樂以外的含義。
然而,該定義的另外兩個部分對它們來說問題更大。關于音樂是一種藝術,具有形式上的屬性,這些屬性值得為其形式而去關注它們,這一觀點可能導致所有的研究趨于同化。在某些方面,為了藝術的第一個定義而去研究技術與技巧,這對于西方的民族音樂學家來說是自然的選擇。如所有音樂家一樣,他們花大量時間獲得音樂制作的技術。當他們聽說其他人創作音樂,他們想去了解音樂是怎樣的,元素是怎樣組合在一起的,以形成連貫的演奏,或者形成一部音樂“作品”。在民族音樂學中,這個關于音樂制作產品的好奇通過大量的音樂分析,或者一定的記譜,或者采用被研究的音樂文化中所使用的記譜法來記寫,這種好奇心被滿足了。
這種細節化的有關音樂作品和音樂演奏形態分析在20世紀80年代后漸漸地失去了興趣,人們在另外的一些問題上更有興趣,即把音樂放在文化和社會中來研究。然而,在近十年中,在作曲家和民族音樂學家麥克·譚澤(Michael Tenzer)的引導下,世界音樂的形態特性分析再顯熱度,他和他的同事在他們的工作中試圖尋找“對音樂結構的刻畫與分析是一種小心翼翼地進入到音樂之中的旅程,去體驗每一次演奏、每一部作品、每一種聲音,把這些作為獨一無二的和結構化的世界,一種優美化了的事件”。(16)
這樣的研究目標使得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定位在了一種西方化的、具有普遍性的藝術是什么的定義之中,這一定位與過去三十年的民族音樂學工作形成了反差。過去三十年的工作是把形態分析作為理解文化的方法,把某種音樂實例作為技術或工藝,一種文化資源,一種社會行為,或其他類似的事情。
仔細觀察音樂作品的特點可以為人類在具體的音樂中是如何具有音樂性的問題提供一種答案,譚澤提出了一種希望,也許能夠引導人們去發現控制人類音樂能力的普遍原則,以此來理解我們的普遍人文精神。
西方的關于藝術定義的最后的部分受惠于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論著《判斷力批判》(1790),該書將藝術與美的、偉大的、優秀的和愉悅的美學評判相關聯。在此影響下,在康德之后,藝術和美學成為了同類詞。這個將音樂視為藝術的觀點給民族音樂學家制造了很多的麻煩。
首先,它把藝術限定在了一種有限的、西方化的觀念之中,即總是把藝術與美相關,忽略了在非西方音樂實踐中所存在的那種非藝術的、功能性的和實用性的藝術。民族音樂學的研究,綜合運用音樂屬性的多重隱喻,展示著即便是西方的音樂藝術,也可能包含著非美學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功能,而且在許多文化中,盡管沒有辦法說成是在全部文化中,都有它們自己獨特的對于好的音樂和美的音樂的評判標準。換句話說,美的確立原則具有文化的獨特性,并非是普遍性的。
在音樂美學的價值評判上有著多種多樣的方式,對其理解方式之一是托馬斯·圖瑞諾(Thomas Turino)的觀點,即:“音樂不是單一的藝術形式,而是……行為上的不同類別,這些行為滿足了人作為人的不同需要以及人作為人所應采用的方式。”(17)他區分了四種不同的音樂藝術:參與性的、表演性的現場演出、高度真實性的和“錄音棚藝術”的音像制品。每一種形式都需要根據它們自身的目標來評判,而不是從單一的或普遍性的觀點來判斷。
這樣的區分忽略了藝術形態屬性的美學評價,也忽略了藝術在情感效果上的美學評價,并且對于民族音樂學家來說產生了另外一個有關藝術定義的問題。比如,在書寫對納瓦霍人(Navajo,美國印第安部落)的音樂研究報告時,大衛·麥克阿萊斯特(David McAllester)記述了他曾問那些被調查的人們當他們聽到一種歌唱時,他們是如何“感覺的”這一問題。麥克阿萊斯特闡述了他所問的有關“美學的和個人愛好”的問題時他是如何思考的。當被調查者做如下的回答時,他感到驚訝,“我很好,我沒什么病啊”。原來音樂是被用來治療身體和心理疾病的,而不是作為審美的享受和專注的對象。他明白了他那些關于審美的問題冒犯了他的受訪人,因為受訪人覺得他在暗示他們得病了。(18)在這種情況下的一種“優秀的”表演,雖有足夠的影響力,但不是去創造審美的享受經歷,而是去治療疾病。
另一種民族音樂學家所采用的將審美和藝術相聯系的方式是解構西方的藝術教育機構,這種被批評家阿爾胡·丹杜(Arthur Danto)所稱的“藝術世界”賦予了藝術和音樂實踐一種藝術作品的身份,換句話說,就是用權威的音樂機構來定義藝術是什么。民族音樂學家墨守成規地在這些機構中教書,如大學中的音樂學院或學院中的音樂系,很多這樣的機構保持了一種藝術世界的狀態,構建著一個特別狹窄的音樂藝術觀念。
把音樂的寓意作為一個有著心理和社會功能的過程或技術來理解;作為一個文化的實踐和社會的行為,與其他的文化和社會行為相一致或相關聯;作為一種文本,為得到其含義而去閱讀;作為一種符號系統,能夠喚起深層的情感和情緒,產生對社會新的理解以及作為一種藝術,成為了民族音樂學家們在研究音樂本質時所做出的貢獻的一部分。
但是,沿著這樣的線索,他們的研究對于音樂僅僅是為了音樂這樣的觀念提出了重要的改進方向,他們以強有力的聲音強調:從古至今,音樂對于人性來說以及在世界上使人作為人類而存在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感謝在翻譯中吾兒張曚給予的幫助——譯者
注釋:
①Richard A.Waterman.1956."Music in Aboriginal Culture-some soc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quoted in Merriam,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p.225.
②Turnbull,Colin M.1961.The Forest Peopl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③Seeger,Anthony.2004[1987].Why Suy á Sing:A Musical Anthropology of an Amazonian People.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quote from p.78.
④Deren,Maya.1984.Divine Horsemen:The Living Gods of Haiti.London and New York:Thames and Hudson.
⑤Bourdieu,Pierre.1977.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⑥Christopher A.Waterman.1982."'I'm a Leader,Not a Boss':Social Identity and Popular Music in Ibadan,Nigeria," Ethnomusicology 26(1):59-71; quotes from pp.67,68.
⑦Leslie A.White.1962.The Puebloof Sia,New Mexico; quoted Alan Merriam,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p.225.
⑧Becker,Judith and Alton Becker.1981."A Musical Icon:Power and Meaning in Javanese Gamelan Music." In The Sign in Music and Literature,edited by Wendy Steiner.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pp.203-215.
⑨Lomax,Alan.Folk Song Style and Culture.Washington,DC: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Lomax,Alan.1976.Cantometrics.Berkeley: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xtension Media Center; quotes from pp.13,17.
⑩Alan Lomax.1968.Folk Song Style and Culture.Washington,DC: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quote from p.133.
(11)Neuman,Daniel M.1980.The Life of Music in North India:The Organization of an Artistic Tradition.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2)Turino,Thomas.1993.Moving Away from Silence:Music of the Peruvian Altiplano and the Experience of Urban Migr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quote from p.77.
(13)Henry Kingsbury.1988.Music,Talent,and Performance:A Conservatory Cultural System.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 quotes from pp.122,123,126.
(14)Thomas Turino.2008.Music as Social Life:The Politics of Particip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quotes from pp.5-16.
(15)Turino,Thomas.1999." Signs of Imagination,Identity,and Experience:A Peircean Semiotic Theory for Music." Ethnomusicology 43(2):221-55; quotes from pp.224,250.
(16)Michael Tenzer,ed.2006.Analytical Studies in World Mus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Thomas Turino.2008.Music as Social Life:The Politics of Particip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quote from p.1.
(18)David McAllester.2006."Reminiscences of the Early Days." Ethnomusicology 50(2):199-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