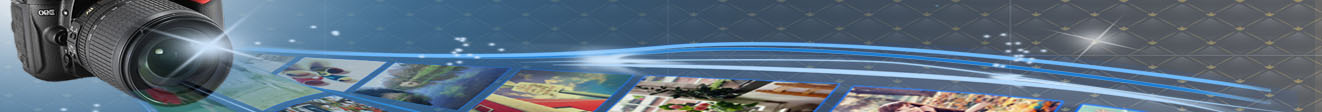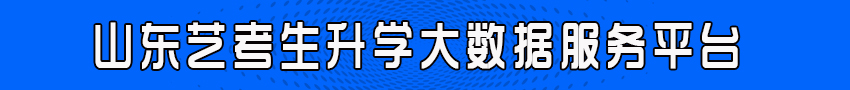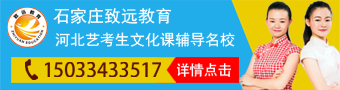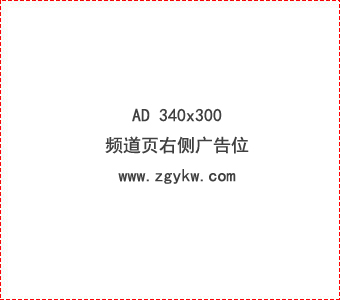尋求形式、題材、音樂語言的高度統一
討論民族歌劇創作發展,首先引發爭論的焦點性問題可能會集中在歌劇的藝術形式問題方面。毫無疑問,用已經有了高度發展并有大量經典留存的西洋歌劇的成功來比對和衡量中國民族歌劇的建構和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在這個比較過程中,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認為,我們的藝術觀念和思維方式中是存在誤區的,即用已經成熟的西洋歌劇的文化藝術形式作為標準衡量我們將要起步或正在初步發展的中國民族歌劇的藝術形式是否健全與合理,這其中包含著思想和理論層面的缺陷。將屬于宏觀層面的文化藝術問題:即中國民族歌劇是否能夠生存所必須要依賴的中國文化傳統基礎和當代中國文化需求至于邊緣,或降低到具體的表現形態層面,而將其他藝術形式提升到標準層面來判斷其能否發展的合理性。其實,歌劇的實質不就是“歌唱的劇”嗎,有誰能斷言,西方或意大利歌劇就是“歌唱的劇”的唯一合理的永恒的歌劇形式,從此世界上再沒可能出現另外的、完全不同的、具有高度藝術標準和同樣成功的“歌唱的劇”呢?我堅信藝術創造的無限可能性,即使我們不能,或暫時不能,不代表后人或未來永遠不能。
就具體的創作問題而言,我認為首先是題材問題。什么樣的題材為好?在過去社會變革、民族救亡等戰爭年代,我們的藝術創作方向在“為誰而莊嚴”方面比較清晰集中,優秀的藝術作品比較容易超越社會各階層喚起全民族的統一情感。而在當前和平社會中,由于藝術作品中“為誰而莊嚴”所煥發的統一藝術力量,容易分散在“為誰而浪漫”的不同的社會群體和不同個性的個人生活或藝術情趣之中。即使是很好的題材很優秀的創作,也很少能產生如過去那樣大的社會影響力。這與其說是當前藝術家們的憾事,何嘗不可以說是反映了新時代藝術創作發展與社會關系的新特點呢。討論藝術題材問題若能客觀面對這樣的變化,亦可發現其中的積極進步,從而探尋和發揚藝術作品能夠超越時代局限并持久保持藝術魅力的積極因素。早期的中國民族歌劇如《白毛女》《江姐》等,很多已經通過了時代變遷的考驗,至今依然為人民所接受。除了藝術層面的成功,如唱段、音樂、劇情等,其劇中弘揚的英雄人物造福民族大我而慷慨犧牲個人小我的獻身精神,符合人類憎惡黑暗崇尚光明的進步思想和共同情感。這種在真善美層面的思想和藝術手段的統一,是其能夠超越時代局限的重要原因。如上所述,題材的選擇應當能夠克服時代變遷的落差,應當有空間在“為誰莊嚴”和“為誰浪漫”獲得更為廣泛的統一。就當前而言,我認為我們應當調整近幾百年中國社會繁變而在我們思想中形成的、判斷時代與藝術關系的習慣性思維。寬放我們“為誰而莊嚴”的時代基點,用中華民族數千年悠久文明成就,豐富“為誰浪漫”的藝術內涵。
在具體的音樂方面,歌的問題往往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性問題。眾所周知,歌劇音樂中“歌”的精彩對于歌劇的成功而言往往事半功倍。一首好聽的歌,往往能傳遍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作曲家、劇作家、詞作家們亦知道這件事情的輕重,竭盡全力為之努力。然而好聽的歌似乎就是這樣可遇不可求。作曲家們創作歌曲的才華為什么在歌劇音樂寫作中表現得不如意?這里面應當引發多方面的思考。
早期的中國民族歌劇中歌的成功,包含藝術成功諸多方面機緣統一。在一個全民族情感和文化生活需求高度統一的時代,諳熟民族音樂的作曲家用擅長的民族音樂語言創作與之表現形式相適應的民族歌劇,就這個意義上講這樣的藝術成就已經達到了這類形式的頂峰,值得我們后來作曲家認真繼承、研究和學習,但是卻不可再復制和超越于當代的歌劇創作之中。面對當前藝術多元化和歌劇音樂語言多元化發展,衡量歌劇中“好聽的歌”的標準和過去也應有大不同。藝術創作存在無限變數的可能,一部滿是精彩唱段的歌劇能夠風靡世界,一部找不到“好聽的歌”的歌劇也可能成為讓人肅然起敬的經典,它們都有藝術價值。因此,我們努力追求創作出“好聽的歌”,卻不應簡單以一般的歌曲標準作為衡量民族歌劇音樂創作的標準,更不應簡單地用“沒有好聽的歌”去抹殺一部原創歌劇作品的全部藝術價值。
世界在變化,時代在發展,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和民族藝術也應在變化中展示新的精神面貌。毫無疑問,民族歌劇創作的發展,應當在這開放的變化中調整姿態,應當有開放的觀念和海納百川的胸懷。我們應努力尋求時代、形式、題材、音樂語言和創作者表演者高度統一,不拘一格地推進中國民族歌劇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