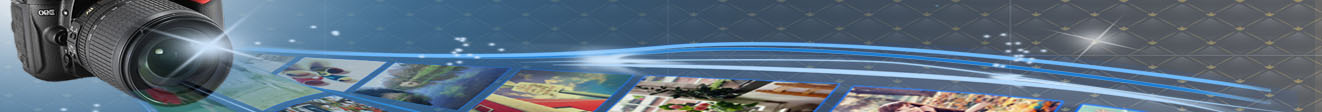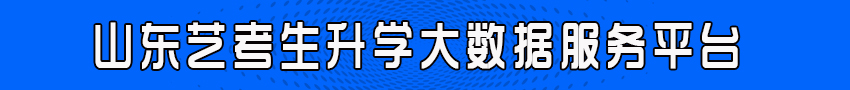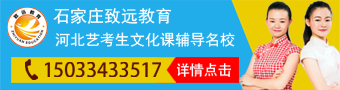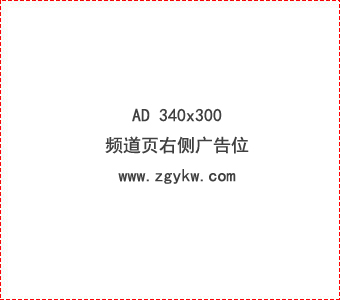跨進21世紀的音樂人類學:國際潮流與中國實踐
【內(nèi)容提要】本文討論當代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范式轉(zhuǎn)移及其在20~21世紀之交的國際潮流和研究路向,梳理歸納出該學科這一時期的主要論題并結(jié)合中國實例說明它們跟音樂實踐和研究的關(guān)系以及當代理論的應(yīng)用。所舉實例包括作者長期考察研究的福州游神樂舞、海南儋州調(diào)聲、黎族民俗音樂、西北花兒等。作者還針對國內(nèi)人類學界和音樂學界的有關(guān)現(xiàn)象進行反思,提出自己的批評和見解,涉及民族、族群、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跨國主義等術(shù)語在英漢對譯上的錯誤與誤讀以及由此導(dǎo)致的學術(shù)表述和研究中的混亂、偽民俗現(xiàn)象以及對待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態(tài)度與做法等問題。
【關(guān) 鍵 詞】音樂人類學/人類學/族群/民族/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民俗/雜合/全球在地化/福州/游神/女子軍樂隊/海南/黎族/儋州/調(diào)聲/國家主義/跨國主義/離散/社會性別/后女性主義/酷兒理論/解構(gòu)/越劇/男旦/后現(xiàn)代理論/后殖民理論
【作者簡介】楊沐,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
[中圖分類號]J6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389(2009)04-0001-019
題記
2009年2月20日,我應(yīng)邀在廣州星海音樂學院給研究生做了一整天的講座,本文即由該講座的前兩部分整理而成,而第三部分《實地考察的新模式》則將另文發(fā)表。本文不是對當代音樂人類學的全面總結(jié)或系統(tǒng)性概述,而是討論音樂人類學在20~21世紀之交的國際潮流并企圖梳理出其中的主要論題,再通過中國實例來說明它們跟音樂研究的關(guān)系,包括我自己的考察研究及思考與見解。限于篇幅,本文所涉實例均為提要式講解,詳盡論述請參閱有關(guān)文論。希望本文能為國內(nèi)相關(guān)專業(yè)的學生提供一些有用的、實實在在的啟發(fā),使其明了國際上當代音樂人類學研究的主要思潮、路向及其運用;亦望文中信息與見解能為國內(nèi)同行提供參考。
我在講座之后收到了美國音樂人類學會學刊Ethnomusicology(《音樂人類學》)2009年第1期。該期在第一、第二篇的重要位置刊出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從當前的學術(shù)角度回顧音樂人類學在20世紀的歷史,涉及對梅里亞姆(Alan Merriam)理論的審視[1],另一篇論及音樂人類學的當前狀況,強調(diào)了當代數(shù)碼革命給本學科帶來的影響[2]。兩篇均為講話式短文,與我講座的具體內(nèi)容不同,當然亦未涉及中國情況;但此二文跟我的講座在思路上卻有相通之處,都強調(diào)本學科當前的新情況。我認為這種思路與時間的巧合并非偶然,它說明了本學科在20~21世紀之交的情況正是當前國際同行普遍關(guān)注并思考的議題,而我那講座恰逢其時。
一、當前國內(nèi)外音樂人類學界的幾個對照
人類社會在20世紀末期已經(jīng)進入了地球村、全球化、高科技、互聯(lián)網(wǎng)、數(shù)碼化、信息爆炸的新時代,各種革命性的當代思潮和理論在思想界和學術(shù)界形成的范式轉(zhuǎn)移大潮已經(jīng)成為不可阻擋之勢。跟其他學科一樣,音樂人類學已經(jīng)順時應(yīng)勢地更新?lián)Q代,不同于20世紀中期了。然而在國內(nèi)的音樂(人類)學界,當前的一些潮流卻跟國際學界的總趨勢大相徑庭。以下從學科建設(shè)、研究路向和論文寫作3個方面各舉一例將國內(nèi)外情況作一對照。
1.學科建設(shè):跨學科拓展—多“學科”林立
就學科建設(shè)而言,國際上的當代趨勢是音樂人類學這一學科在不斷地進行跨學科的拓展,不僅已跟人類學、社會學等其他人文和社會學科相融匯,而且已有涵括西方歷史音樂學的趨勢。在歐美音樂(人類)學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xiàn)了一些在新概念指導(dǎo)之下的研究,例如“feminist musicology”(女性主義音樂學)與“queer musicology”(酷兒音樂學),但是它們只被看作是音樂(人類)學學科之內(nèi)新拓展出來的研究領(lǐng)域(field of study),而不是自立新學科(new discipline)的意思。在大學里,這些新的研究領(lǐng)域可能被設(shè)置為音樂(人類)學專業(yè)中的一個新課程,但通常卻不被認為是獨立的新學科。這一發(fā)展,其實是跟國際上整個學術(shù)界當代的跨學科拓展、多學科互融的總趨勢相順應(yīng)的。具體的情況,僅從音樂人類學領(lǐng)域中最大的兩家國際性學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國際傳統(tǒng)音樂學會)和Society for Ethnomusicology(美國音樂人類學會)每屆學術(shù)會的論文以及這兩家學會的刊物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傳統(tǒng)音樂年刊》)和Ethnomusicology(《音樂人類學》)各期的論文就可以看出。我亦曾在國內(nèi)發(fā)表文章對相關(guān)情況作過論述(例見參考文獻[3]),此處不贅。
反觀國內(nèi)情形,音樂學術(shù)界近年來卻不是向外拓展而是向內(nèi)分裂,本來就已經(jīng)孤立狹小的音樂研究這一畝三分地界之內(nèi),卻如群雄割據(jù)似地裂變?yōu)槎唷皩W科”林立。學者們熱衷于各分自留地、創(chuàng)立各種各樣的某某“學”,似乎已經(jīng)形成一種時髦。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90年代后期至今的10多年間,音樂研究領(lǐng)域內(nèi)各種名目的“學科”越來越多,令人眼花繚亂。其中少數(shù)是此前原有的,其余的有些是從國外借鑒來的,更多的則是國內(nèi)學者自創(chuàng)的。傳統(tǒng)的西方歷史音樂學、音樂美學之類不說,僅僅在實際上本來可被音樂人類學這一個學科涵蓋的范圍之內(nèi),國內(nèi)出現(xiàn)的“學科”就有: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中國音樂學、音樂文化學、樂律學、音樂形態(tài)學、樂種學、民族樂器學、音樂心理學、音樂治療學、音樂文學、音樂考古學、音樂圖像學、音樂教育學、音樂社會學、音樂音響學、音樂翻譯學、音樂批評學、旋律學、音樂文獻學、音樂傳播學、音樂現(xiàn)象學、音樂應(yīng)用學、音樂分析學、音樂詩學、音樂語言學、音樂解釋學,等等;除此之外,還有不少沒有冠以“某某學”名號的“學科”與上述諸多“學”分庭抗禮,例如“音樂藝術(shù)管理”、“中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世界民族音樂”、“東方音樂研究”等。這種創(chuàng)立新“學科”的趨勢目前仍然勢頭正盛,新名目仍在繼續(xù)出現(xiàn)中。這個趨勢的直接結(jié)果是:一方面,既然創(chuàng)立了這么些“學科”,則每個“學科”就得有獨立于其他“學科”之外的“學科創(chuàng)始人”、“學術(shù)帶頭人”、“學科”傳承人,還得有專攻本“學科”的專家學者,當然在音樂院系中也就得設(shè)立相應(yīng)的專業(yè)、開設(shè)相應(yīng)的課程、有本專業(yè)的碩導(dǎo)博導(dǎo)、招收本專業(yè)的研究生。另一方面,各“學科”紛紛設(shè)立專屬本“學科”的獨立學會,其中會長、副會長、常務(wù)理事、一般理事等等學術(shù)官職一應(yīng)俱全;然后名正言順地申請公款召開這個“學”那個“學”的學術(shù)會議,由本“學科”的官員、專家和學者與會。這種情況,固然可以看成是國內(nèi)音樂學園地中百花齊放、欣欣向榮、形勢一片大好;但卻也可以看成是一種令人擔憂的山頭林立、因神設(shè)廟、各自畫地為牢的現(xiàn)象。各音樂院校的“學科”和專業(yè)五花八門、架床疊屋;這樣的“學科”越分越細,專業(yè)越來越多,越細越專,越專越孤立。與歐美國家綜合大學內(nèi)設(shè)置音樂系的傳統(tǒng)不同,國內(nèi)在綜合大學內(nèi)設(shè)置音樂系的做法才剛剛起步,原先的傳統(tǒng)就是音樂院校孤立于綜合大學之外,其教師和學生躲在象牙塔內(nèi)自成一統(tǒng),綜合素質(zhì)普遍偏低,而在如此褊狹的象牙塔內(nèi),如今又新增了如此繁多且還繼續(xù)增多的“學科”各自割據(jù)、自我封閉,情形就更加惡化了。國內(nèi)曾有個別學者跟我談過類似問題,而在我的上述講座之后,另一學者亦發(fā)表過一篇文章,論及音樂學科建設(shè),認為國內(nèi)音樂院校對學科的認識不統(tǒng)一,很多是重復(fù)設(shè)置或者矛盾對立,專業(yè)認同的混亂對學科建設(shè)無益且浪費學術(shù)資源[4]。然而在國內(nèi)音樂學術(shù)界,上述狀況目前尚無改變的跡象。
2.研究路向:當代論題熱—梅里亞姆熱
1964年,美國音樂人類學者梅里亞姆發(fā)表了里程碑式的專著《音樂人類學》[5],提出了著名的音聲、概念、行為三要素理論。這一理論此后成了音樂人類學研究的經(jīng)典模式。歐美的音樂人類學界本來就很強調(diào)對音樂進行采錄、記譜而后據(jù)此對音聲本體做形態(tài)分析,從中歸納總結(jié)音樂形態(tài)的規(guī)律;而梅氏理論則為當時的音樂人類學研究拓展了視界,除了音聲,把概念和行為也納入了研究重點,并企圖發(fā)現(xiàn)三者之間的聯(lián)系。但在梅氏理論出現(xiàn)之后直至梅氏1980年去世,歐美音樂人類學界曾經(jīng)陷入一個誤區(qū),即狹義而機械地認為音聲跟人類思維、行為和其他社會因素之間必定存在很具體的、一一對應(yīng)的形態(tài)上的聯(lián)系,而研究者的任務(wù)就是要找出這些具體聯(lián)系及其規(guī)律。梅氏理論提出的時候,正是現(xiàn)代主義思潮最強盛然而也最接近強弩之末的年代。那時的學者普遍遵循現(xiàn)代主義的話語體系,認定人類社會和文化的發(fā)展跟自然界一樣,必然遵循某些既定的規(guī)律,而學者的任務(wù)就是要通過考察研究來發(fā)現(xiàn)社會和文化的本質(zhì)、從中找出這些恒定不變的規(guī)律。在音樂研究中,這就相應(yīng)地是要找出音聲的本質(zhì)與規(guī)律,梅氏理論由此應(yīng)運而生。但是緊隨其后,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登上學術(shù)舞臺,挑戰(zhàn)現(xiàn)代主義理論的主角地位。在人類學界,以吉爾茲(Clifford Geertz)為代表的闡釋學派影響日增,學者們不再注重對人類社會和文化“發(fā)展規(guī)律”的尋求,轉(zhuǎn)而著重于對人類不同社會和文化的考察、闡釋、理解和溝通。進入21世紀,后現(xiàn)代主義思維已經(jīng)在學術(shù)界形成遠比現(xiàn)代主義思維更為強勢的潮流。音樂人類學界的研究路向在梅氏之后也隨之而轉(zhuǎn),越來越多的學者不再熱衷于尋找音聲本質(zhì)和“規(guī)律”,而著重于如何理解、如何闡釋音樂文化。音樂人類學的重心轉(zhuǎn)移到對人類音樂文化中各種社會論題的研討,例如探討音樂文化中顯示的族群性、身份認同、社會性別、全球化現(xiàn)象等。21世紀的音樂人類學已經(jīng)不再是梅氏時代的音樂人類學了。
反觀國內(nèi)學界的現(xiàn)狀,則與此大不相同。一方面,目前國內(nèi)音樂(人類)學的主流仍然強調(diào)對音聲本體的研究,以音樂活動為對象而未著重音聲本體的研究常常遭到批評,這樣的博碩士論文甚至可能因此被否決;另一方面,不少學者在研究和教學中過分強調(diào)梅氏理論的學習和運用而相對忽略了國際上當前音樂人類學界的主流。若把國內(nèi)這一現(xiàn)象稱為“梅里亞姆熱”,或許并不為過。梅氏熱若出現(xiàn)于20世紀中期,可說是恰逢其時,但出現(xiàn)于21世紀,則未免給人落伍的感覺。在這一熱潮的影響與誤導(dǎo)之下,今天國內(nèi)相關(guān)領(lǐng)域內(nèi)不少學生,在談?wù)搶W術(shù)話題時幾乎是三句話不離梅里亞姆,似乎梅氏思路就是當代音樂人類學研究的唯一正道,而對當前國際上學術(shù)路向的主流知之甚少。事實上,對于這些80后甚至90后的學生來說,梅里亞姆是爺爺輩的人物了,梅爺爺主要理論的提出,距今已有半個世紀。誠然,梅氏理論在音樂人類學史上樹立了一座豐碑,他的理論已經(jīng)成為經(jīng)典,一直有應(yīng)用價值,但畢竟他是上一個時代的學者了,他在幾十年前提出的理論已經(jīng)不足以代表當前音樂人類學的理論思潮,當代學界的研究思路早已越出了他的思維體系而大為拓展了。今天的音樂人類學者,應(yīng)該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若在理論認識上固步自封于梅氏時代而不求更新,甚至還只是自封于對梅式理論的機械式理解的淺層次里,那對研究沒有益處。而今天的教師們?nèi)粼诮虒W中忽略這一點,則會貽誤后學。
3.論文寫作:論題式文化研究—綜述式文化志寫作
在歐美學術(shù)界,學術(shù)研究向來強調(diào)論題(issue)研討,音樂人類學界也不例外。實際上多數(shù)國家學術(shù)界在這一方面的情況也都如此,只是隨著學界的理論范式轉(zhuǎn)移,目前與先前學界所關(guān)注的論題有所不同而已。在20世紀上、中期,音樂人類學研究的論題多跟音樂現(xiàn)象的“規(guī)律”有關(guān),而20世紀晚期以來學者們關(guān)注的論題卻更多地是跟闡釋與理解音樂文化現(xiàn)象有關(guān)。在強調(diào)論題研討的趨勢中,不帶分析研究的單純描述型的音樂文化志、調(diào)查報告和綜述、概述固然可以說是學術(shù)考察或者情況總結(jié)的成果,但通常卻不被看做是學術(shù)研究的成果。因為,所謂研究,就不能只是單純的描述,而必須在考察報告的基礎(chǔ)上還有理論性的分析、研究和據(jù)此得出的結(jié)論。這通常要求研究者集中探究一個或幾個論題,還必須是有學術(shù)意義的、前人沒有探討過或者尚未得出結(jié)論的論題、有新發(fā)現(xiàn)或新見解而非重復(fù)前人的觀點或成果。這是學術(shù)研究論文寫作的基本要求之一。然而國內(nèi)學界卻沒有這樣的共識,一些學術(shù)刊物的編輯或院校里的教師甚至自己都沒有這樣的學術(shù)意識,也就談不上據(jù)此來分辨論文類別、評判論文質(zhì)量或指導(dǎo)論文寫作。在國內(nèi)學界,調(diào)查報告式或情況綜述式的博碩士論文并不鮮見;一些已經(jīng)當了碩導(dǎo)博導(dǎo)的學者,自己的博碩士論文或者所從事的“研究”就是這種情況,則其指導(dǎo)的博碩士論文情況如何就不難想見。具體的實例很容易找到,我在這里就不指名道姓公開舉例了。當然,如果國內(nèi)這種情況的存在只不過是因為國內(nèi)學界不贊成國外學界在這一方面的共識而認為單純描述型的文章、報告、綜述之類也應(yīng)該算做研究成果、也可以作為博碩士論文,那就又當別論,只能說是國內(nèi)學界有意遵循跟國外學界不同的學術(shù)規(guī)范而已了。
二、國外當代音樂人類學中的熱點論題
如前所述,國外當代音樂人類學的研究重心已從尋求音樂文化的“規(guī)律”轉(zhuǎn)移到為理解、闡釋音樂文化而進行的各種論題研討。下面我把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國外本學科內(nèi)常見的論題作一梳理,粗略地歸納成幾個類別,分別結(jié)合我自己或其他學者對中國音樂文化的考察研究實例加以說明,同時也針對性地反思國內(nèi)實踐并提出我的見解。
1.族群、族群性、身份認同、國家主義、跨國主義
“族群”(ethnic group)這一術(shù)語于20世紀中期在歐美人類學界出現(xiàn),在20世紀后期被國外學術(shù)界普遍采用,取代了早先的術(shù)語“種族”(race)和“部族”(tribe,又譯“部落”)。這一更改,反映了當代學界相關(guān)認識的變更。在早先的術(shù)語及其概念中,“種族”區(qū)分或“部族”區(qū)分所強調(diào)的是血緣與親屬制的異同,而當代的“族群”區(qū)分卻不以此為主要依據(jù)。族群的分野跟民眾自己的族群歸屬感和族群身份認同(identity)密切相關(guān);同一族群的成員共同選擇不同于其他族群的文化標識,例如語言、衣著、生活方式和習俗,以示跟其他群體的區(qū)別;而族群、族群性(ethnicity,又譯“族性”)、族群身份或認同以及族群區(qū)分都是可變的、流動性的,就連文化的異同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且不見得跟族群的異同有必然的或固定的聯(lián)系。在這種認識之下,歐美人類學界在20世紀80年代就對中國的民族劃分持有異議,并對中國人類學界將“民族”一詞及其概念挪用于學術(shù)研究的做法提出批評[6]。在中國大陸,個人的民族身份是由官方認定的,無法憑個人的自由選擇和歸屬感來決定。雖然民族身份鑒定在理論上也注意到群體文化的異同,但在實際操作中,血緣卻被作為最重要依據(jù):一個群體的民族身份一旦被劃定,則永世不可變更,其成員的民族身份也世代不可變更。一個國家基于某種原因——例如政治或行政管理上的需要——而依據(jù)某種標準和命名對本國人口做此類劃分,這無可非議。但是倘若學術(shù)界把這樣的行政分類及其標準、命名、定義和概念分毫不變地照搬到人類學和文化研究中作為學術(shù)分類標準和學術(shù)概念,那就可能產(chǎn)生大問題。而中國國內(nèi)學界的情況卻正是如此,由此導(dǎo)致的問題也顯而易見。舉例而言,在“民族”概念的主導(dǎo)之下,半個世紀以來,國內(nèi)學界普遍認為民族的區(qū)分跟文化的異同相符合,卻沒有重視到,文化各異的不同族群可能被劃歸同一個民族因而被誤認為具有共同的文化,而同一文化的某個族群卻又可能被分劃到數(shù)個不同的民族之中因而被誤認為文化不同。另一方面,民族身份固定不變的概念很自然地導(dǎo)出各民族的文化本身以及相互之間的區(qū)分也是固定不變的結(jié)論。這些都跟國際上當代學界對族群和族群文化的認識相悖。我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起,就在數(shù)篇文章中談到上述問題,希望引起國內(nèi)學界的重視[7][8][9]。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我又指出,雖然“族群”術(shù)語在21世紀已經(jīng)傳入國內(nèi)人類學界,但在對“族群”與“民族”概念異同以及取舍的討論中,卻“至今無人討論這些弊端,現(xiàn)狀是既想跟上‘族群’概念,但又不敢否定‘民族’概念;在舊概念破不了、新概念立不起的窘境中,目前的普遍做法是生拉硬扯地試圖證明二者共存的合理性,致使族群課題研討中出現(xiàn)理論上難以自圓其說的尷尬局面”。[3]與此現(xiàn)狀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另一個問題是某些中西術(shù)語的誤讀、誤譯和誤用。在20世紀50年代,由于國內(nèi)的“民族”定義和鑒別所遵循的是當時斯大林的相關(guān)理論,自那時起國內(nèi)對“民族”一詞的正式英譯一直是“nation”或“nationality”。然而這卻是明顯錯譯,但這一嚴重錯誤在國內(nèi)卻至今未被重視也未被承認。這兩個英譯完全忽略了一個事實:在中文里“民族”沒有“國家”的意思,但在英語中“nation”與“nationality”這兩個詞的首要意思卻分別是“國家”與“國籍”而非族群與族群身份。國內(nèi)的這種錯譯和概念的混淆又直接導(dǎo)致了另外兩個中譯的錯誤,即把本意是“國家主義”的英文術(shù)語“nationalism”翻譯成“民族主義”,把本意是“跨國主義”的“transnationalism”翻譯成“超民族主義”。術(shù)語翻譯的錯誤直接導(dǎo)致概念理解和運用上的錯誤。然而所有這些錯誤同樣沒有在國內(nèi)學界引起足夠的注意,國內(nèi)學者們?nèi)匀黄毡樵谶@些錯譯和錯誤理解國外術(shù)語、概念和理論的基礎(chǔ)上來翻譯國外著述、討論相關(guān)的理論課題,由此更進一步導(dǎo)致一系列相隨而來的翻譯上和理論上的錯誤,把原本就是從西方引進的當代族群理論攪得更加糊涂。但在上述“民族”英譯的根本錯誤以及學界濫用“民族”概念的弊端未被正視、甚至在討論中被有意回避的情況下,這些錯誤和混亂繼續(xù)存在,而且已經(jīng)成為糾纏不清的死結(jié)。可以想見,在相關(guān)的外文新術(shù)語新概念不斷出現(xiàn)的情況下,國內(nèi)學界如果堅持不從根本上認清上述誤譯并予以糾正,那么將會在誤讀誤解誤用外文術(shù)語的歧路上越走越遠,一路錯下去,相隨的錯誤和混亂還會繼續(xù)并且加深,最后將弄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20世紀上半葉,許多人想當然地認為,隨著全世界的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族際交流、國際交流、文化開放和互融等程度的加強,世界上不同族群之間的矛盾以及國家主義等問題會逐漸淡化。但是其后的歷史事實證明,這種情況非但沒有出現(xiàn),而且族群身份、族群性、國家主義等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還更形突出,許多地區(qū)動亂的根本原因都跟族群沖突有關(guān)。在人類學領(lǐng)域,自20世紀60年代末期以來,族群性成了中心議題之一,到了21世紀,它仍然是一個研究重點,其中族群文化自然是一個重要方面。作為族群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音樂跟族群性、族群標識、族群身份、文化標識、文化認同等方面的關(guān)系,也就成為當代音樂人類學者普遍關(guān)注的重要論題。我曾撰文討論過一些實例,比如海南黎族樂器作為族群文化標識及其跟族群身份的關(guān)系[10]、“性愛音樂活動”跟族群身份和文化認同的關(guān)系[11]等,大家可以參閱。在此類論題的研討中,較易于被國內(nèi)學生忽略的要點之一是:族群身份跟人們自身的歸屬感和選擇有關(guān),族群標識和文化標識也常常是人為的選擇和人為的建構(gòu)。但在“民族”概念長期教導(dǎo)和濡染之下的國內(nèi)學子,容易傾向于把作為族群標識的音樂文化理解成既定的、固定的、在不同族群之間相應(yīng)地不同的、界限分明的東西,而忽略了它其實是可變的、流動性的、由族群成員選擇的人為構(gòu)建這一關(guān)鍵點。從國內(nèi)現(xiàn)有的著述和教學情況來看,音樂學界的學者和教師至今仍然固守“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分類概念和思路,從來無人對此提出異議或有過質(zhì)詢,未見觀念更新的跡象。而國內(nèi)的人類學界,雖然存在前述問題,畢竟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已在運用國外當代學界的“族群”術(shù)語和概念。就這一點而言,國內(nèi)的音樂研究界落伍于國內(nèi)的人類學界甚多。我認為,國內(nèi)音樂研究界長期以來自閉于社會科學界之外,是形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之一。
國家主義經(jīng)常表現(xiàn)出族群的性征,二者之間既有相似性,又有根本區(qū)別。區(qū)別國家主義和族群性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國家有領(lǐng)土、有疆域、有政府、有警察或軍隊,而族群卻沒有這些。國家主義者認為本國文化的疆界必須跟國家的疆界相關(guān)聯(lián),而族群沒有領(lǐng)土的要求,因而也不強調(diào)這樣的理念。族群運動中一旦出現(xiàn)了領(lǐng)土和疆界訴求,則從定義上說,這種運動就成為國家主義運動了。國家主義為了全國的凝聚力而強調(diào)國內(nèi)文化的相同或相似性,同時強調(diào)跟國外文化區(qū)分,以示內(nèi)外有別。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是由多族群和多文化組成的,但卻由某一個強勢族群主政。主政的族群會把本族群的語言和文化制定為本國的國家語言和文化,或者把它們作為構(gòu)建“國家文化”的主體或藍本,同時行使國家權(quán)力來推行、維護與強化這種人為構(gòu)建的“國家文化”。這就是國家主義的實例之一。音樂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不可能超然于外,因此音樂文化與國家主義的關(guān)系也是當代音樂人類學的熱門論題之一。比如各國國歌,就可以說是國家主義的產(chǎn)物。音樂文化中的國家主義論題研究,跟中國音樂相關(guān)者可舉一位臺灣學者的論文為例。該文研討20世紀下半葉京劇在臺灣的狀況,研究當時在臺灣執(zhí)政的國民黨政府如何利用京劇作為工具來為自己的國家主義目的服務(wù)。京劇被有意識地定名為“國劇”,在臺灣國民黨政府的資助和扶植下,作為中國的國家文化代表在國際上到處巡演,為臺灣國民黨政府營造一種維護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形象,進而宣揚該黨該政府才是中國文化的正統(tǒng)傳承人和保護人、才是中國的合法代表。[12]其實,在臺灣不僅國民黨政府如此。在臺灣民進黨執(zhí)政期間,該黨的“臺獨”主張就曾直接導(dǎo)致該島文藝政策的相應(yīng)轉(zhuǎn)向。當時臺灣政府的文藝基金和扶助對象完全傾斜到臺灣本土文化,源于大陸的京劇在臺灣的“國劇”地位不再,而臺灣的本土文化,包括本土音樂,則被民進黨政府宣揚為臺灣的“國家文化”,跟該黨把臺灣營造為一個國家的企圖密切呼應(yīng)。這是國家主義與音樂關(guān)系的又一個實例。
在西方,“transnationalism”(跨國主義)這個術(shù)語雖在20世紀初期就已出現(xiàn),但它被學術(shù)界普遍運用卻是相當晚近的事。它稍早被用于經(jīng)濟研究中,討論全球化狀況中出現(xiàn)的跨國商業(yè)和跨國經(jīng)營等現(xiàn)象,例如為減低成本、擴大產(chǎn)銷而建立的跨國公司,以及跨國經(jīng)營中為適應(yīng)當?shù)厍闆r而出現(xiàn)的產(chǎn)品及銷售等方面的調(diào)整與變化。21世紀初期以來,這一術(shù)語和概念被人文和社會學科借用于研討文化現(xiàn)象。音樂人類學界雖然也相隨跟上,把音樂文化的跨國主義納入關(guān)注論題,但至今明確使用這一術(shù)語和概念對音樂進行考察研究的著述卻仍然很少,不過研討對象實質(zhì)上屬于跨國主義現(xiàn)象的論文倒有一些,實例可見下文“福州游神樂舞”一節(jié)中相應(yīng)段落提及的文章。
2.人口遷徙、離散
人口遷徙或人口流動(human mobility)的概念不難理解,但是明確地以此為論題來討論音樂文化的論文,在國內(nèi)卻未見或少見。其實,這個論題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在日常生活中相關(guān)的題材很多很常見,只不過好像大家沒有加以注意,正所謂“天天看,看不見”。比如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nèi)眾所周知的農(nóng)民工現(xiàn)象就是人口遷徙的實例。隨著經(jīng)濟改革開放大潮,各地鄉(xiāng)村農(nóng)民大量涌入城市打工掙錢,在城市里成為雖然松散但卻人數(shù)巨大的群體。在不少地區(qū),這種情況對城鄉(xiāng)民間音樂文化產(chǎn)生了直接影響,以下舉出兩個實例。我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對西北和海南的民俗音樂研究持續(xù)了30年,期間進行了多次實地考察,下面兩例分別取自甘肅蘭州和海南儋州。
實例1.西北花兒:
花兒原先主要流傳于西北鄉(xiāng)村地區(qū)。直至80年代初期,在大城市里,例如蘭州市區(qū),市民們在日常生活中是見不到實際發(fā)生于民眾生活中的花兒對唱活動的。但是此后隨著進城農(nóng)民工的增多,情況發(fā)生了變化。農(nóng)民工在打工之余難有其他娛樂,于是自然而然地以自己鄉(xiāng)間的花兒演唱活動自娛,經(jīng)常聚在市內(nèi)的公園、廣場等處對唱花兒。這樣的活動越來越頻繁,聚集的規(guī)模越來越大,形成了市區(qū)公共文藝活動的一道新興風景線,吸引了大量市民。這種在日常生活中直接呈現(xiàn)的、當面互動的、活生生的音樂,給市民們的感受相當生動強烈,那是文藝舞臺上或廣播電視里的表演所無法比擬的。耳濡目染之下,城里的花兒愛好者迅速增多,逐漸從觀賞進而參與,花兒創(chuàng)作和演唱活動也因此在市區(qū)民眾中流傳開來,市民中甚至出現(xiàn)了自發(fā)組織的花兒演唱愛好者協(xié)會。每年鄉(xiāng)間的“花兒會”,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城里人前往參加。另一方面,鄉(xiāng)間的一些演唱者得知花兒演唱在城里受歡迎的情況之后,便自發(fā)組隊到城里的公園、廣場等公共場所表演花兒對唱,以圍觀群眾自發(fā)投幣的方式收費,類似于傳統(tǒng)藝人的街頭演藝。這些都是原本的花兒傳統(tǒng)中不存在的、由當代的人口遷徙導(dǎo)致的新現(xiàn)象。
實例2.海南儋州調(diào)聲:
調(diào)聲是海南儋州方言區(qū)的一個歌種。直至80年代中期,調(diào)聲演唱及其賴以生存的“后生家籠”和“夜游”習俗都只在當?shù)剞r(nóng)村存在,而且僅限于未成家的青少年參與,其主要社會功能是尋求性伴侶。成家之后的村民既不參與調(diào)聲演唱,也不介入后生家籠生活,更不參與夜游;而城市里也不存在這些習俗與活動[13]。但是從80年代后期開始,這種情況發(fā)生了根本變化,而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當?shù)剜l(xiāng)村青年尤其是未成家的青年大量離開農(nóng)村,進城打工。原來儋州方言區(qū)農(nóng)村的習俗是未成家的青年們集中在本村的后生家籠住宿,調(diào)聲演唱和夜游就是這些青年們的主要娛樂;后來他/她們絕大部分離開自己的村子,后生家籠解體,而其他變化,例如村民居住條件的改善使得成年子女可以在自家居處有自己的臥室與活動空間、手機互聯(lián)網(wǎng)摩托車等交往工具的家庭化普及和流行歌廳舞廳咖啡店夜市等娛樂交往處所的濫觴,也都使得青少年之間的結(jié)交聯(lián)絡(luò)與往來便捷而且范圍擴大,調(diào)聲和夜游活動及其功能都被更加方便、更為豐富多彩的當代活動方式所取代。到了20世紀末,當?shù)卦鷳B(tài)的調(diào)聲演唱活動已經(jīng)隨著后生家籠和夜游習俗共同消亡。但在同一時期,當?shù)卣畢s把調(diào)聲作為本地文化品牌,鼓勵并組織調(diào)聲的創(chuàng)作與演唱并定期舉行全市范圍的調(diào)聲比賽。由于原生態(tài)的調(diào)聲文化已經(jīng)消亡而且留在農(nóng)村的未成家青年所剩無幾,于是新的調(diào)聲創(chuàng)作和演唱活動就成為與上述民俗傳統(tǒng)完全無關(guān)的、由當?shù)毓俜劫Y助和組織的、以中老年人、城鎮(zhèn)及國營企事業(yè)單位職工以及專業(yè)表演團體表演的當代文化構(gòu)建,其內(nèi)涵和社會功能也跟傳統(tǒng)調(diào)聲文化的內(nèi)涵和功能有了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
離散(diaspora)是指同一族群全體或者其中人口數(shù)量足以形成獨立社區(qū)的群體由于某種共同的原因,自愿或被迫地在同一時期向某一異文化的地區(qū)或異國遷徙。這種遷徙常常比較遠程。這一群體在遷至該處定居后未被當?shù)匚幕耆纬勺约旱纳鐓^(qū),保留了自己的故土文化和傳統(tǒng),并且傳承給后代,使其母體族群文化和傳統(tǒng)在當?shù)鼐S持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作為人類學術(shù)語,“離散”跟“人口遷徙”或“移民”都有區(qū)別。“移民”泛稱任何遷徙的個人或群體,“人口遷徙”的概念則更加松泛,它們都不一定指稱離散現(xiàn)象或離散族群。比如說,上述農(nóng)民工現(xiàn)象屬于人口流動或人口遷徙,但卻不是離散現(xiàn)象;近年來成千上萬的中國學生到國外留學,其中不少人成為移民,但是并未在該國形成統(tǒng)一的族群社區(qū),因此這也不是離散現(xiàn)象。換句話說,離散的族群可以被泛稱為移民,但在很多情況下移民卻不是離散族群。零星的、分散的、時間地點原因各自不同的人口流動都是人口遷徙而不是離散,而在同一文化同一社會中不同地區(qū)的遷徙,即使是人口數(shù)量較大的集體遷徙,也只是移民而不是離散。例如近年來由于三峽水庫的興建而從庫區(qū)舉村遷至鄰近新村安家的村民被稱為“三峽移民”但卻不被認為是離散族群。
離散族群在與當?shù)匚幕拈L期接觸與交流中,所保留的故土文化不可避免地會發(fā)生相應(yīng)的變化。所以,文化的離散研究常常涉及文化雜合(見下文)方面的議題。此外,離散研究還常常涉及族群性、族群身份認同、文化認同、國家主義、跨國主義、全球化、全球在地化等論題。在音樂文化的離散研究中,這些也同樣都是值得關(guān)注的方面。必須注意,在商業(yè)化、旅游化或全球化進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人口跨國流動、異國文化交流以及異國文化活動,在多數(shù)情況下跟離散現(xiàn)象或離散文化不是一回事,不要把二者混為一談。比如說,來到中國的某國商人、投資者、外交人員、企事業(yè)人員、旅游者以及求學者在某一城市或區(qū)域人數(shù)較多,于是在當?shù)刂饾u出現(xiàn)這些人常去的聚集點例如某一個或幾個會所、酒吧、餐館之類,而這些場所也因此設(shè)置或組織一些為這些人服務(wù)的文化項目或活動,例如該國音樂的表演。這些人群、場所和文化因素在中國都是臨時的、階段性的、無聚居地的、高流動性的、不穩(wěn)定的,根本沒有形成長期的、相對穩(wěn)定地保留其母國文化和傳統(tǒng)的社區(qū)。不要把這種流動性的松散人群誤認為是離散社區(qū),也不要把這樣的文化活動誤認為是離散文化。對這樣的場所、人群及其活動的考察研究,也不能算是離散研究。對其中的音樂活動的考察研究,當然也不是音樂文化的離散研究。
3.表述、話語、權(quán)勢、邊緣化
這幾個都是后現(xiàn)代理論中的術(shù)語和概念。在當代社會科學界,包括音樂人類學界,后現(xiàn)代理論已經(jīng)成為學者和學生必須掌握的基礎(chǔ)知識,我此前也已在國內(nèi)的文章和講座中多次做過介紹(例見參考文獻[14][15]),這里就不再重復(fù)講解這些概念和理論,而只談它們在音樂人類學中的應(yīng)用。
音樂是一種表述(presentation)形式。我們所研究的音樂,比如一個歌種或樂種,它表述什么、如何表述、在怎樣的話語體系(discourse)中進行表述、跟當時當?shù)氐闹髁髟捳Z體系是否有沖突、或者有怎樣的相互影響、人們?nèi)绾瓮ㄟ^這樣的表述進行交流,等等,都是值得研討的論題。表述跟話語和權(quán)勢(power,又譯為霸權(quán))都密不可分,同時還經(jīng)常牽涉到邊緣化現(xiàn)象(marginalization)。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舉出我對“性愛音樂活動”的考察研究作為實例[11]。在中國法定的56個民族中,超過半數(shù)在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或者現(xiàn)在仍然存在我所界定的這種“性愛音樂活動”習俗,就是通過演唱演奏來尋找性愛的習俗,是當?shù)匦运椎囊徊糠帧5菑男运捉嵌葘@種音樂活動進行考察研究的論述卻除了我的論文之外,國內(nèi)未見其他著述,某些文章即使涉及類似活動,也都避而不談它的性愛及性俗的內(nèi)涵和功能,而以其中不一定存在的“愛情”代之。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我認為是由于這種習俗跟漢族主流話語(例如儒家話語)中的道德標準相悖,在漢族主流話語的權(quán)勢之下,這些性俗被界定為“不道德”的習俗而被邊緣化了。正如儒家話語中的“非禮毋聽,非禮毋視”,其實“非禮”的現(xiàn)象并非不存在,只不過它被儒家話語霸權(quán)界定為“非禮”所以被強行排除在公眾的視聽范圍之外,在公眾中造成了它不存在的印象。在霸權(quán)籠罩之下,這些被邊緣化的現(xiàn)象自然未能被公開報道,而深受主流話語霸權(quán)控制或影響的學術(shù)界,也就無人對此做專項研究并公開討論。即使是參與這些活動、傳承這些習俗的當?shù)厝耍渤T谥髁髟捳Z的權(quán)勢威壓之下對外人三緘其口,通常不會對外人坦承當?shù)赜写肆曀住1热缯f,西北地區(qū)的花兒民歌習俗,其傳統(tǒng)實質(zhì)是通過對唱尋求性愛,花兒中有許多唱詞內(nèi)容是相當直露地表達或描述性愛的。但由于被漢族主流話語的霸權(quán)視為“色情”和“陋俗”,當?shù)厝瞬粫p易對外人演唱這樣的歌詞,也不會對外人坦承花兒習俗的性愛內(nèi)涵。我在當?shù)氐亩啻慰疾熘校贾皇钱斘腋數(shù)厝艘呀?jīng)打成一片、不再被當作外人看待之后,他/她們才會放心地唱出這些歌詞并且跟我講述活動內(nèi)情。被邊緣化的社會現(xiàn)象,往往并不是真正的邊緣現(xiàn)象,也就是說不見得真是在社會上非常少見的、無代表性的、可被忽略的現(xiàn)象;相反,它們常常是多見的、有代表性的、不應(yīng)被忽略的、一點也不邊緣的現(xiàn)象。花兒的性愛內(nèi)容即為一例。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常常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從前被我們忽略的重大研究課題。例如,在男權(quán)中心主義的社會中,女性現(xiàn)象以及女性話語都是被男權(quán)中心主義話語的霸權(quán)邊緣化掉的弱勢群體和弱勢話語,基于這一認識去觀察社會上的音樂文化,就可能發(fā)現(xiàn)不少先前被我們忽略的、被邊緣化了的女性課題。
4.科技、媒體、傳播
當代科技(technology)、媒體(media)和傳播(communication)跟音樂的關(guān)系非常密切,但是在國內(nèi)音樂(人類)學刊物上發(fā)表的這方面研究論文卻很少。國內(nèi)的大眾傳播專業(yè)領(lǐng)域內(nèi)有少量以音樂為考察對象的相關(guān)文章或者以此為主題的博碩士論文,不過研討的對象都是當代流行音樂而不是民俗或傳統(tǒng)音樂(例見張武宜、殷瑩論文[16][17])。國外的音樂人類學界,涉及這些論題的研究也多是以當代流行音樂為研究對象的,涉及民俗或傳統(tǒng)音樂的也較少。我認為,當代科技、媒體及傳播例如互聯(lián)網(wǎng)、數(shù)碼技術(shù)、廣播電視跟流行音樂的關(guān)系固然顯而易見,但是它們對民俗音樂或傳統(tǒng)音樂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對后者的研究論文少,應(yīng)該只是因為學者們尋找研究題材的眼光過于專注在顯而易見的流行音樂上,卻忽略了對民俗音樂的觀察。比如說,不論國內(nèi)外音樂人類學界,學者們對民歌的定義向來都跟“口頭創(chuàng)作、口頭傳播”的說法離不開。但是在當代,一方面由于文盲日漸減少、城鄉(xiāng)差別縮小,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媒體和傳播的發(fā)達,特別是互聯(lián)網(wǎng)和數(shù)碼化的日漸普及,民歌的創(chuàng)作和傳承已經(jīng)越出了口頭文化的范圍,這種情況在中青年之中更容易見到。近年來國內(nèi)許多地區(qū),包括不少農(nóng)村,電腦、互聯(lián)網(wǎng)和視訊以及相關(guān)的制作與使用都已相當普及,很多人喜歡把本鄉(xiāng)本土的民歌、民樂以及相關(guān)的民俗活動制成數(shù)碼音像保留、贈友或上載到互聯(lián)網(wǎng),使其廣泛傳播。例如下文討論的福州“游神”樂舞,就可以從“優(yōu)酷”、“土豆”之類的視頻網(wǎng)站找到當?shù)厝松陷d的第一手錄像。另外,國內(nèi)各大網(wǎng)站上都有社區(qū)性質(zhì)的版塊或部落格,其中有些已成為各地民歌創(chuàng)作、交流、討論和傳播的方便渠道,比如新浪網(wǎng)的天涯社區(qū)海南版塊中就有儋州山歌和調(diào)聲的繁榮園地。我自己在考察研究中曾從互聯(lián)網(wǎng)獲益不少,對此我將另文撰述;但在學術(shù)界,我卻尚未見到對這些現(xiàn)象進行研討的著述。
5.環(huán)境、生態(tài)
僅就傳統(tǒng)概念中的音樂而言,直接以環(huán)境(environment)和生態(tài)(ecology)作為中心論題的著述,在國內(nèi)外的音樂研究中都不多見。不過當代學界已經(jīng)把研究的范圍擴大到自然和人為的音響例如風聲雨聲、蟲鳴鳥叫、車鳴人喧。這些音響本身就是環(huán)境和生態(tài)的組成部分。其實,即使僅限于傳統(tǒng)概念上的音樂范圍,值得以此為題進行研討的音樂或音樂現(xiàn)象就不少,問題是我們沒有加以應(yīng)有的注意和思考。顯而易見的實例可舉專業(yè)創(chuàng)作或民間音樂中以自然、生態(tài)或環(huán)保為標題或內(nèi)容的作品。當然,如果僅把討論局限于這么具象而淺顯的范圍,那未免對此類論題的理解過于膚淺或表面化。我們還應(yīng)該更進一步考慮音聲、音樂現(xiàn)象或音樂活動跟環(huán)境和生態(tài)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我在海南黎族音樂的考察中就曾發(fā)現(xiàn)這樣的實例:黎族人相信在稻谷結(jié)穗時吹奏該族的氣鳴樂器“唎咧”能夠得到神靈保佑風調(diào)雨順、使稻谷生長旺盛[10];而在為播種清理山地之前必須唱“砍山歌”祈求山靈樹靈的原諒[18]。這些音樂現(xiàn)象都有環(huán)保的內(nèi)涵,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又如,宗教的起源、形成和發(fā)展跟人類所處的環(huán)境和生態(tài)直接相關(guān),作為宗教活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宗教音樂也不例外。比如,祈雨的樂舞、祈求豐收的儀式音樂,就都是宗教音樂跟環(huán)境與生態(tài)直接相關(guān)的實例。其實,在中國的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中,音樂跟自然環(huán)境和生態(tài)密不可分,這在中國的古典音樂、傳統(tǒng)音樂和民俗民間音樂實踐中都有所表現(xiàn)。中國的古典哲學與美學崇尚自然,講究天人合一。作為修身養(yǎng)性的音樂,更是強調(diào)這些內(nèi)涵。在中國傳統(tǒng)的音樂思維中,五音跟五行對應(yīng),律呂跟君臣對應(yīng),音樂中也講陰陽。這樣的思維不僅在樂音和音樂形態(tài)中有所體現(xiàn),就連樂器的形制、樂隊的組構(gòu)、演唱演奏的技法、音樂的應(yīng)用等等也常與此相關(guān)。除此以外,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把考察與研究的視域和思路從自然環(huán)境和生態(tài)擴展至社會與人文的環(huán)境和生態(tài),而這一方面又跟下面要講到的政治和政策方面的論題有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例如中國歷史上音樂的形態(tài)、建制及其應(yīng)用就跟皇朝政策、宮廷政治、家族政治、祭祀政治等密切關(guān)聯(lián),也常常跟社會體制、階級地位分不開。這些方面的實例,學過中國音樂史的學生應(yīng)該都知道。有著深厚歷史傳承的中國當代民俗音樂和傳統(tǒng)音樂,自然也繼承了這些觀念和哲理,包括音樂的審美觀、功能觀和象征意義等等。
6.政治、政策
政治(politics)和政策(policy)與音樂文化之間的關(guān)系應(yīng)該比較容易理解。畢竟,國內(nèi)大陸學者和學生自20世紀中期以來必學的也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就強調(diào)政治跟文藝密不可分,而有些專題領(lǐng)域,比如說中國近現(xiàn)代音樂史,跟政治的緊密關(guān)系也的確是再明顯不過的。但是,在其他專題領(lǐng)域內(nèi),例如在當代民俗音樂或當代流行音樂的研究中,國內(nèi)出版物中就極少或未見明確討論政治論題者。這種狀況的形成固然有客觀原因,但是研究者主觀上對政治敏感話題心存忌諱而有意無意地避免涉及,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其實,即使在這些專題領(lǐng)域,目前國內(nèi)學者們可以公開研討的政治和政策題材還是很多的。下面從我自己的民俗音樂研究論文中舉出幾個論題實例以供參考:
(1)政治跟民歌實踐與研究的關(guān)系[19]:“文藝為無產(chǎn)階級政治服務(wù)”、“以文藝作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武器”之類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宣傳、推廣、普及和實施,給全國范圍內(nèi)的民歌、傳統(tǒng)器樂、戲曲和曲藝音樂的創(chuàng)作、表演和傳播造成的巨大影響與后果,這些意識形態(tài)對民間音樂的采錄、收集、整理、出版以及考察和研究所產(chǎn)生的導(dǎo)向性影響與后果。
(2)國家政策跟民歌、傳統(tǒng)樂器和器樂以及傳統(tǒng)戲曲和曲藝之間的關(guān)系[10][18][20][21]:在20世紀中期,“公有制”、“公私合營”等政策對民間藝人的組織、經(jīng)營方式、表演方式、技藝傳承等方面的直接影響和后果;“大躍進”、“科學化”跟中國傳統(tǒng)樂器改革的關(guān)系;“破除迷信”跟民間宗教音樂或民俗信仰音樂存亡的關(guān)系;“以糧為綱”、“機械化”、“合作化”與“公社化”等農(nóng)業(yè)政策對一些與農(nóng)作方式共生的民歌和器樂消亡的關(guān)系;“移風易俗”跟一些與民俗共生的民歌或器樂存亡的關(guān)系;20世紀末期實施的一系列改革開放政策對傳統(tǒng)音樂的影響。
(3)政治跟音樂人類學學術(shù)研究及學科發(fā)展之間的關(guān)系,前者對后者產(chǎn)生的導(dǎo)向性影響及其后果[22]。
7.經(jīng)濟、商業(yè)化、商品化、消費、旅游業(yè)
包括所有學科在內(nèi),國內(nèi)已經(jīng)出版的著述中以經(jīng)濟(economy)、商業(yè)化(commercialization)、商品化(commodification)、消費(consumption)或旅游業(yè)(tourism)為議題對音樂進行討論者已有相當數(shù)量,但絕大部分都是比較空泛的議論式短文。而且,即使包括未出版的博碩士論文在內(nèi),研討的對象也僅限于當代流行音樂和中國音樂史范圍之內(nèi)(例見參考文獻[23][24][25])。然而在實際生活中,與此類論題相關(guān)的音樂現(xiàn)象卻并非只能在這兩個領(lǐng)域內(nèi)見到。例如,就民俗音樂而言,歷史上器樂、說唱、戲曲等向來就是民間藝人賴以生存的一種商品,在此意義上也是民間大眾的一種消費品。而在當代社會,這種情況更加明顯,加上當代旅游的普及和旅游業(yè)的興盛,民俗文藝作為旅游業(yè)的重要賣點,民俗音樂商品化的現(xiàn)象也就比先前任何時代都要普遍。這些現(xiàn)象又跟當代的人口遷徙、科技、傳播、政治、政策、全球化、雜合化等因素緊密相關(guān)。許多原本沒有經(jīng)濟功能的民俗音樂,在這些當代因素的沖擊和影響下,迅速具備了經(jīng)濟或商業(yè)功能,比如前面提到的海南儋州調(diào)聲。直至20世紀80年代初期,調(diào)聲是完全沒有經(jīng)濟功能的,跟商業(yè)、商品全都無關(guān)。但在其后的經(jīng)濟改革開放與商業(yè)化大潮之中,在當?shù)卣某珜?dǎo)、組織和資助下,當?shù)貙I(yè)演藝團體和民眾被組織起來表演調(diào)聲以彰顯本地文化、吸引外地旅游者。調(diào)聲及其演唱被利用為當?shù)芈糜螛I(yè)的重要品牌和招商引資的廣告手段,變成了一種以經(jīng)濟功能為主的文化商品。與此同時,在這種社會氛圍中,民間自發(fā)出現(xiàn)了以商業(yè)營利為目的的、半專業(yè)的調(diào)聲演唱隊,在當?shù)孛癖娭斜环Q為“專業(yè)調(diào)聲隊”。當?shù)剞r(nóng)村人年節(jié)慶典、結(jié)婚、生子、孩子上大學、新房落成等喜慶場合,常喜歡雇請這些“專業(yè)調(diào)聲隊”來表演助興,儼然成了一種新興民俗。但由于前述的當?shù)厍嗄甏罅侩x開農(nóng)村這一情況,這些“專業(yè)調(diào)聲隊”的成員就主要是已經(jīng)成家的而且還留在本鄉(xiāng)的中年人。因此,這一新興民俗除了演唱的詞曲和表演形式還保留了原生態(tài)調(diào)聲的因素以外,其他各方面已經(jīng)跟傳統(tǒng)的調(diào)聲民俗完全不是一回事了。類似的實例在全國很多,前述的西北花兒也是如此。花兒及其演唱在傳統(tǒng)上也是沒有商業(yè)功能的,但在20世紀末期,一方面,當?shù)卣疄榱税l(fā)展旅游,把花兒作為當?shù)氐奈幕放仆瞥觯瑸榱宋慰汀⒃黾勇糜螛I(yè)收入而組織花兒演唱并把傳統(tǒng)上完全是民眾自發(fā)的“花兒會”改變?yōu)橛烧M織民眾參與的聚會;另一方面,則是前面說過的民間自發(fā)組成的小型花兒表演隊靠巡演花兒營利。這些也都是傳統(tǒng)的花兒文化中沒有的商業(yè)行為。
在對國內(nèi)民俗音樂的實地考察過程中,我還發(fā)現(xiàn)一個跟商業(yè)化、民俗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有關(guān)的問題,有必要提請學術(shù)界和有關(guān)部門重視。這里涉及兩個概念:其一,什么是民俗;其二,當前聯(lián)合國號召保護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指的是什么。
民俗是民間的風俗習慣,是民眾自發(fā)參與實踐的傳統(tǒng)習俗而不是政府行為,一般沒有任何官方的介入。即使某種民俗的初始起源跟官方行為或命令有關(guān),它也需要經(jīng)過較長的歷史時期,例如數(shù)百年,最終積淀為民間大眾無需官方組織命令而自然遵循并實踐的習俗,這才成為民俗。當前由官方規(guī)定目的、內(nèi)容、時間、地點與做法、通過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地要求并組織專業(yè)人員和民眾參加和從事的活動,尚未在民間積淀為無需由官方介入而被民眾普遍地自發(fā)遵從、實踐的風俗習慣者,根本不是民俗。對民俗的這種認知應(yīng)該算是常識,但是,在國內(nèi)當前的現(xiàn)實中,這么簡單的常識卻常常被忽略了,甚至在學術(shù)界也如此。
聯(lián)合國號召保護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指的是代代傳承下來的、至今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的傳統(tǒng)文化,其中有不少是瀕臨滅絕的種類,如果不及時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其中許多可能就會真正滅絕,所以,我們要集社會之力對其加以保護、維持,讓其繼續(xù)存活下去。但是,如果一個文化品種在當前現(xiàn)實生活中已經(jīng)滅絕,那么它就已成歷史,是一種史料。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這樣的史料多不勝數(shù)。對這樣的史料或已然滅絕的民俗,我們固然可以調(diào)集人力財力對其進一步挖掘研究,甚至為某種目的而試圖恢復(fù),但是它們卻不屬于聯(lián)合國所要撥款保護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范圍,自然也不應(yīng)該無中生有地立項申請確認為所謂“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以進行莫須有的“保護”。更不應(yīng)該人為地構(gòu)建出目的內(nèi)涵和功能都完全不同的偽民俗來冒充文化遺產(chǎn)以達到獲取經(jīng)濟利益的目的。
但是當前國內(nèi)某些地區(qū)的某些做法卻與上述認識相悖。這里從我30年來持續(xù)考察研究的海南音樂文化中舉一實例。海南黎族一些地區(qū)存在一類傳統(tǒng)的歌節(jié),在特定的日期,人們聚集在特定的地點,對唱情歌,借此尋找性愛伴侶。這是黎族的一種歷史悠久的民俗[9][11]。各黎族支系中對這種歌節(jié)的黎語叫法不同,當?shù)貪h人多按漢族習慣以漢語稱之為“三月三”。黎族的這種歌節(jié)完全沒有經(jīng)濟和商業(yè)功能,也完全沒有政治功能。從1949年底開始,在極左意識形態(tài)主宰下,黎族的這種民俗被認為是“陋俗”,受到壓制而迅速消亡,60年代“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后則被全面禁止繼而滅絕。到了社會政治氛圍較為寬松的80年代初期,這種民俗在少數(shù)黎區(qū)先有恢復(fù)勢頭,但緊接著在其后的改革開放大潮中再度消失,其主要原因是這一期間黎區(qū)不論在自然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方面都疾速起了翻天覆地的巨變,而黎族的這種傳統(tǒng)歌節(jié)原本就是跟當?shù)貍鹘y(tǒng)的自然、社會和人文因素互為因果、共生共存的,傳統(tǒng)因素的消失或巨變導(dǎo)致了這種歌節(jié)習俗從黎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完全絕跡。換句話說,在黎區(qū),原生態(tài)的這種歌節(jié)習俗已成歷史,而不再是活生生的現(xiàn)實存在,不應(yīng)該被認為是聯(lián)合國當前所要保護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然而,當?shù)卦?0年代中期卻出現(xiàn)了一種由官方組織的節(jié)日聚會和表演,名為“海南國際椰子節(jié)”[11]。組織者明確規(guī)定這個節(jié)日的思路是以文化活動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策略是文化搭臺、經(jīng)貿(mào)唱戲,最終目的是招商。其后,這種由政府自上而下地策劃、安排并組織民眾參與的節(jié)日被以漢語更名為“黎族三月三”,其終極目的是創(chuàng)建當?shù)氐奈幕放埔晕慰秃屯顿Y、發(fā)展旅游以及招商。很清楚,這種人為構(gòu)建的活動是政府行為,而不是民俗。但是,當?shù)卣畢s把這種人為構(gòu)建的節(jié)日確認為“黎族民俗”,以此向國家有關(guān)部門申報為省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而且居然通過了上級有關(guān)部門的審核,被確認為是黎族民俗并被授予“省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稱號。這種做法,是在真正的原生態(tài)黎族歌節(jié)民俗已經(jīng)事實上完全消亡的情況下,以目的、內(nèi)涵和功能都完全不同的一種當代人為構(gòu)建物來李代桃僵。這一替代品是一種偽民俗,確認它為“民俗”是一種誤導(dǎo),確認它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一個錯誤。這個問題倘若不予以澄清,將繼續(xù)誤導(dǎo)子孫后代。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一旦被確認為“文化遺產(chǎn)”,當?shù)赜嘘P(guān)方面都認為這是一種榮譽和生財之道,紛紛對其加以利用,以它作為當?shù)匾詾闃s的文化品牌,大作廣告,為開發(fā)旅游和招商引資的目的服務(wù),據(jù)此發(fā)展出各種旅游項目和文化商品以獲取經(jīng)濟效益。
在全國范圍內(nèi),“黎族三月三”不是一個孤立的實例。近年來全國各地熱烈申報“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目,其中不難發(fā)現(xiàn)上述問題。與此緊密相關(guān)的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對待真正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態(tài)度和做法問題。按理說,對于貨真價實的、目前還活著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我們應(yīng)該竭盡所能對其加以保護,但是一些地方部門,卻為了迎合當代旅游者的口味和喜好或投資者的商業(yè)目的,不遺余力地使用大量非傳統(tǒng)因素將其改造得面目全非,結(jié)果是在“保護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口號下,在政府的撥款資助下,反而把原生態(tài)的遺產(chǎn)破壞殆盡。這種對待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態(tài)度和做法,跟聯(lián)合國保護遺產(chǎn)的本意是背道而馳的。在這一方面,國內(nèi)雖然也有某些學者意識到存在的問題,但由于不便明言的種種原因,公開指出這些問題的學者卻是鳳毛麟角。下面引述我在國內(nèi)僅見的一則公開言論,是歷史學者陳春聲在一個講座中的答聽眾問,說得很有見地:
我們有一個錯覺,就以為上了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是一個榮譽,就像奧運會得了金牌一樣,其實不是。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評世界文化遺產(chǎn),是在交代一個責任,就是這個東西不能破壞,要保留下來。從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來說,這不是授予你一個榮譽,而是交代你辦一件事,只是這件事值得交代給你,這個很重要。……他們相信地方政府真的有足夠的能力把它保護下來,留一些文化基因,他就同意把這個責任交給你。其實他們不僅是想這些東西的優(yōu)點在哪里、價值在哪里,而是把這個責任交給你。所以,評上世界文化遺產(chǎn)就馬上開發(fā)旅游是錯誤的,因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是不太能開發(fā)做旅游的。上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是因為專家們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就交代給你保護,如果你保護得不好,就從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里把你的名字去掉。就是你要知道,這個東西不是榮譽,而是一個非常大的承諾和責任,這是最重要的。[26]
國內(nèi)音樂人類學界的專家學者有責任對上述問題予以重視并在實踐中加以解決。中國文化部明示:“經(jīng)中央編辦批準成立的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研究保護的專門工作機構(gòu)——中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中心就設(shè)在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它在對全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資源普查、國家名錄體系的建立、科學保護工作的指導(dǎo)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還承擔著文化部委托的向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作’的論證、評選工作”[27]。現(xiàn)在一些音樂方面的偽民俗已經(jīng)被確認為國家級或省級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這不得不說是上述工作中的嚴重失誤。這種失誤又說明了評審者對所評音樂民俗的實情了解不足且對聯(lián)合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界定認知不足。國內(nèi)評審就有此失誤,則在此基礎(chǔ)之上論證出來的向聯(lián)合國申報的本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作,可信度堪虞。如何糾正此類失誤、如何保證今后不再出現(xiàn)此類失誤、如何對待已被評定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目,顯然是一個急迫而嚴峻的課題。
8.社會性別、女性主義、后女性主義、酷兒理論
“社會性別”是英文術(shù)語“gender”的中譯。在當代文化理論中,“社會性別”跟“性別”(sex)所指不同。性別是生理和體質(zhì)上的區(qū)分,而社會性別的概念是社會的人為建構(gòu),是在某一特定社會和文化里,由該社會的文化和傳統(tǒng)所規(guī)范的性別角色。在不同的社會和文化中,對社會性別角色的概念和分類常常是不同的。比如說在許多社會里,“男性”被認為是強勢的、主宰的、能夠在社會上肩挑重任的角色,而“女性”則被認為是柔弱的、順從的、能夠做家務(wù)的角色。然而在另外一些社會里,由于傳統(tǒng)和文化的不同,所謂“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卻可能與此不同甚至相反。比如在摩梭人的母系社會中,女性的社會角色就被認為應(yīng)該是強勢的、能夠擔當社會和家庭重任的,與父系的漢族社會中的社會性別概念相悖。所以說,社會性別概念和分類,主要是由社會傳統(tǒng)和文化決定的,一個人的社會性別應(yīng)該是怎樣一種角色,得看她/他所處的社會和文化對男女角色的概念如何,而不是她/他的實際生理性別如何。我們從小在某一特定的社會和文化中生活,潛移默化地接受了這個社會的社會性別觀念,以至于“理所當然”地認為它是天生如此、本該如此的,而從來沒有想到,自己以為“本該如此”的觀念,其實不過是這個社會的文化建構(gòu),根本不是天生如此的。所以,在學術(shù)研究中,我們應(yīng)該特別小心,不要先入為主地戴著某種文化中心論的有色眼鏡而不自知。
在音樂研究中,社會性別是一個內(nèi)容十分豐富的論題。音樂在社會性別的建構(gòu)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所發(fā)揮的功能、所產(chǎn)生的社會意義,都是廣闊的考察研究領(lǐng)域。但在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中,社會性別的題材卻常常被社會上的主流話語給邊緣化了,而我們在此影響之下,則常常習慣性地忽視了很多可做課題的音樂文化現(xiàn)象。例如,傳統(tǒng)歌種、樂種有的只由男性表演而有的只由女性表演,京劇的男旦、越劇的女性男角等現(xiàn)象都很值得研究,但在國內(nèi)音樂研究界,這些現(xiàn)象卻很少有人涉獵,或是雖然涉及但卻仍然秉持舊時代的思路而未循當代社會性別研究的視角和路向進行研究。以女性主義(feminism)路向為例,這是當代社會性別研究中的一種常見路向,研究者跳出傳統(tǒng)的男性中心主義成見,從女性的角度對研究對象進行考察和思考。這樣的換位思考可能使我們發(fā)現(xiàn)被成見遮蔽的現(xiàn)象與論題,得出更加符合實際或更加深刻的結(jié)論。但是,如果你所秉持的是男性中心主義的觀點、立場和視角,那么即使你的研究對象是女性現(xiàn)象,你的研究和結(jié)論仍然是男性中心主義的。當然,我們在研究中也不應(yīng)該矯枉過正,不要從男性中心主義泥潭中跳出,卻一頭栽進了女性中心主義泥潭。采取女性主義的路向和理論來從事研究,跟秉持女性中心主義來做研究,是不同的兩回事。此外,我們在研究中采取女性主義路向或者研討女性論題時,不要忽略了后女性主義(postfeminism)思潮。了解這一思潮以及它跟女性主義的區(qū)別,有助于我們認識到女性主義的不足之處,使我們在有關(guān)的研究中思路更為嚴謹。女性主義是現(xiàn)代主義的產(chǎn)物,后女性主義則跟后現(xiàn)代思潮相關(guān)聯(lián)。后女性主義于20世紀60年代萌芽,90年代大行其道。它對女性主義進行反思和質(zhì)疑,認識到女性主義自身的問題和自相矛盾的思維模式。比如說,女性主義追求全球統(tǒng)一的、有別于男性的女性整體身份,但同時卻又追求與男性的無差別完全平等,這是自相矛盾的。再如,女性主義預(yù)設(shè)女性“應(yīng)該有”的“正確”態(tài)度并強加于人,忽視了不同社會的文化差異,抹殺了女性的個人意愿,剝奪了她個人自由選擇的權(quán)力。后女性主義認識到,并非在所有的社會中女性都是受男性欺壓的犧牲品;女性和男性有別,而女性本身又是多元的、千姿百態(tài)各不相同的,不存在全世界完全一樣的所謂“女性整體”;任何女性都可以自主決定她如何做一位女性,而不必遵從任何預(yù)設(shè)的、一體化的、“正確的”女性態(tài)度和行為;后女性主義鼓勵婦女探索和體驗自己性本體的復(fù)雜性。
酷兒理論(queer theory)也是社會性別研究中的重要理論。酷兒理論始于同性戀研究,后來升華為當代的文化理論,被借用于人類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學術(shù)領(lǐng)域,并影響到文學、美術(shù)、音樂、舞蹈、戲劇等領(lǐng)域的實踐。酷兒理論其實不是某一個單一的理論,如果把它看作包括如下原則的思路或思潮,我們會覺得更加容易理解,運用于研究中也更容易得心應(yīng)手:
·解構(gòu)主義思維
·抵制異性戀中心主義
·以多元的態(tài)度對待世界
·從多元的視角觀察了解世界
·關(guān)注邊緣現(xiàn)象和邊緣化現(xiàn)象
·恢復(fù)被邊緣化者的應(yīng)有地位
國內(nèi)有些學生可能對什么是解構(gòu)主義不大了解。極簡略極淺白地說,不論一篇文字還是任何人或事,都是一個文本,而任何一個文本都可能有多種不同的解讀,但人們卻常常習慣性地只采納某一主流話語的“正統(tǒng)”解讀,認為那是天經(jīng)地義的、理所當然的解讀而從來沒有想過其他可能的不同解讀。解構(gòu)主義思維就經(jīng)常使用與“正統(tǒng)”不同的,甚至是“離經(jīng)叛道”的卻又符合邏輯的思路來解讀和詮釋文本,因此得出的結(jié)論也常常出人意料,甚至被正統(tǒng)觀念視為異端或者另類。
現(xiàn)在我舉一個實例來說明上述幾個原則的運用。大家都知道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對這一故事的傳統(tǒng)解讀,是男女之間誓死不分離的凄美愛情故事,是男女主角以死來抗議封建包辦婚姻的悲劇。這種解讀,是在異性戀中心主義的社會中,人們“自然而然”地只站在異性戀的立場、只以異性戀中心主義的定性思維來觀察和理解一切社會現(xiàn)象的結(jié)果。但是如果站在抵制異性戀中心主義、秉持多元的態(tài)度和視角等原則的立場上,對這個故事做解構(gòu)式的解讀,我們卻能得出不同的闡釋。其中之一是:這是同性戀者梁山伯竭力擺脫異性戀者祝英臺單相思追求的故事,是在異性戀中心主義的社會里經(jīng)常發(fā)生在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之間的悲劇,有著典型的、代表性的社會意義,是社會性別論題的一個生動題材。不過,遍尋國內(nèi)出版物和網(wǎng)絡(luò),我僅僅見到文化學者朱大可在2005年從這一角度解構(gòu)《梁祝》和越劇的一篇議論文[28](對該文跟風附議的網(wǎng)文不計在內(nèi)),卻未見從這一思路來對這一劇目和劇種作深入研究的學術(shù)論文。朱在該文中談到:《梁祝》“是經(jīng)過偽飾的同性戀范例,顯示了中國同性戀文化和美學的基本特征,但這一長期流傳于吳越乃至長江流域的悲劇,同時也是話語誤讀(或掩蔽)的一個范例。從被言說和傳播起,直到在越劇中擴充與定型,‘梁祝’一直遭到異性戀話語的闡釋,以致它的真實語義被長期歪曲,并且以后還將被繼續(xù)歪曲下去。梁祝故事之所以遭到誤讀,乃是由于其主要角色是一對男女。消除這一語誤的方式,就是運用同性戀語法對文本展開重讀”。他通過符合邏輯的闡釋,以他所說的“同性戀語法”令人信服地解構(gòu)了《梁祝》文本,繼而評論說:“在結(jié)構(gòu)和元素沒有受到任何毀壞的前提下,僅僅變換了一種密碼,我們就獲得了有關(guān)梁祝故事的全新版本。這與其說是一次標新立異的闡釋行為,不如說是對梁祝故事的語義還原”。在我自己從音樂人類學的角度對越劇和《梁祝》的思考中,更多地是把它跟中國傳統(tǒng)戲曲中的社會性別論題相聯(lián)系,其中,演員和角色的社會性別置換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論題。確實,不止是越劇,也不止是《梁祝》,在京劇等其他劇種中,不論在實際表演和劇目角色中都存在男女社會性別置換的現(xiàn)象,比如京劇的男旦傳統(tǒng),比如豫劇的《花木蘭》劇目。在越劇里,《梁祝》是一位女扮男裝的女異性戀者跟一位男同性戀者之間的戀愛悲劇,而這位女扮男裝的角色祝英臺和這位男性角色梁山伯卻又都由女性演員扮演。在這里,演員的社會性別在表演實踐中做了置換之后在劇情之中被再一次置換,我把這種現(xiàn)象稱為社會性別的“雙重置換”(在英文中我把它稱為“double twist”)。比起京劇男旦現(xiàn)象,越劇《梁祝》所展示的這種表演實踐和劇情內(nèi)容疊置的社會性別雙重置換的文本更能引起我的學術(shù)興趣。如果說在男權(quán)中心主義的傳統(tǒng)中國,男旦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是一種社會必然的話,那么為何少數(shù)劇種中卻相反地出現(xiàn)了女性表演的生角甚至凈角,甚至京劇本身也曾出現(xiàn)過女凈?為什么偏偏在江浙的社會和文化生態(tài)中孕育出越劇這樣全女性出演的劇種并且它在當?shù)孛癖娭虚L期受到歡迎形成強勢存在的當?shù)貞蚯鷤鹘y(tǒng),即使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極左思潮指導(dǎo)之下強制性的戲曲改革也沒能把這一傳統(tǒng)根除?而為什么又偏偏是《梁祝》這一綜合了同性戀和女扮男裝題材的劇目在這樣一個以社會性別置換作為表演實踐特征的劇種中成了最成功的保留劇目?換言之,社會性別的雙重置換現(xiàn)象出現(xiàn)于越劇,有什么社會原因、什么社會意義?作為一種社會表述,它說明了什么?在上面引述的朱大可文章中,朱的評述重心雖然不在這些方面,但是他卻在文中針對《梁祝》成為越劇的代表性劇目這一社會現(xiàn)象表達了他的思考,認為“梁祝故事與越劇的這種親緣,還因為其演員都由女性擔綱”。他認為越劇是女同性戀美學的民間產(chǎn)物,并認為:“真正重要的事物也許并不在戲臺之上,而是在戲臺的四周。一方面是戲曲演員的言說影響了觀眾的言說(傾聽)方式,一方面是觀眾對戲曲話語的強有力的設(shè)定,這場圍繞舞臺所展開的對話是沒有邊界和終結(jié)的,但支配戲曲語法的終極之手肯定不是表演者,而是那些臉龐隱沒在黑暗中的民眾,他們的趣味支配了戲曲。在民眾的指引下,越劇沿著同性戀的方向勝利前進,達到了它們在上世紀中葉的高潮”。這里的可貴之處在于他把《梁祝》文本的內(nèi)涵和展演跟社會、文化和民眾聯(lián)系起來了。
上面這個實例演示了解構(gòu)以及酷兒理論一些原則的應(yīng)用。它碰巧涉及一個跟同性戀有關(guān)的題材,但我們必須注意,酷兒理論并非只在同性戀題材的課題中應(yīng)用,它的原則和思路是可以廣泛運用于多種人文和社會學科的研究中的,包括音樂人類學許多題材的研究。
9.雜合、雜合化、地方化、全球化、全球在地化
“雜合”或者“雜合性”譯自英語“hybridity”。這個術(shù)語及概念在語言學中的歷史不短,但是當代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雜合”(cultural hybridity,又譯“文化雜合性”)術(shù)語及概念則只在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流行,這跟同時期流行的后殖民理論(postcolonial theory)有關(guān)。在后殖民理論出現(xiàn)之前,學術(shù)界在殖民主義研究中普遍認為殖民者文化與殖民地文化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只是前者向后者的單向侵入或滲透,而該過程導(dǎo)致的只是后者的消亡或被前者同化。但后殖民理論認為,二者的關(guān)系并非只是如此簡單的單向過程和單一結(jié)果;二者之間的滲透是雙向的,其結(jié)果也是多樣的。在殖民過程中,殖民者文化在侵入殖民地的同時,不但會遇到草根性極強的當?shù)匚幕蛡鹘y(tǒng)各種不同形式的、或明或暗的抵制,而且會受到后者的反噬、被后者滲透。這種雙向互動的結(jié)果并非一定是其中一方的消亡或被彼方同化,而是經(jīng)常出現(xiàn)文化雜合現(xiàn)象,生成文化雜種(cultural hybrid),甚至形成新的傳統(tǒng)。而在殖民地生成、繁衍的雜種或新傳統(tǒng)還可能反向植入到殖民者的本土文化之中扎根、生長,最終也成為殖民者本土社會中的文化新種甚至成為該社會的新傳統(tǒng)。在英文術(shù)語中這樣的雜合過程是“hybridisation”,中文譯為“雜合化”。當然,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文化雜合現(xiàn)象的研究已在整個社會科學領(lǐng)域內(nèi)成了重要課題而不再局限于對殖民和后殖民現(xiàn)象的研究。雜合現(xiàn)象在音樂文化中也很普遍,因此,在歐美國家的音樂人類學界,文化雜合自20世紀末以來也成為時興的議題。但在國內(nèi),至今為止研討雜合現(xiàn)象的著述卻仍然大多集中在翻譯界及語言學界,而在社會科學界則很少見。至于國內(nèi)的人類學界和音樂(人類)學界,相關(guān)的研究更少,在音樂研究中明確地論述或運用這一特定術(shù)語和概念的著述,我個人尚未見到。
地方化(localisation)、全球化(globalisation)和全球在地化(glocalisation)這3個概念都跟雜合有關(guān)。地方化和全球化這兩個概念近年來在國內(nèi)時常聽到,也比較容易理解,我這里就只著重講講全球在地化概念。在英文里,“glocalisation”是個新造的合成詞,繼“globalisation”(全球化)一詞之后出現(xiàn);它由“globalisation”(全球化)與“l(fā)ocalisation”(地方化)二詞的頭尾拼合而成。由于中文里從未有過跟“glocalisation”相應(yīng)的術(shù)語和概念,該術(shù)語的中譯就成了一個難題。現(xiàn)有的中譯五花八門,極不統(tǒng)一,如:“全球地方化”、“全球-地方化”、“全球本土化”、“全球-本土化”、“全球在地化”、“全球地域化”、“本地全球化”、“本土全球化”、“全球化下的本土化”、“地方化中的全球化”、“球土化”、“球域化”等等。這些中譯有的不知所云,有的差強人意,倘若僅僅根據(jù)字面意思,都無法準確推衍出英文原文術(shù)語所代表的概念,都必須另加說明才行。而在英文中,“glocalisation”的字面意思是比較清楚的,懂得英文的人一看就明白這是“全球化”與“地方化”的并列結(jié)合(globalisation+localisation),二者沒有先后或主次之分。然而,在中文里,不論是“全球地方”也好,“地方全球”也罷,只要是“地方”和“全球”兩個詞一先一后地擺在一起,就容易被理解為是定語和主語,有主次之分而不是并列關(guān)系,無法準確表達出英文里“全球+地方”二者并列的意思。由于中文構(gòu)詞上的性質(zhì),更理想的中譯或許事實上是不可能達成的,只好指望國內(nèi)各界能夠在現(xiàn)有譯名中盡快地約定俗成出一個相對而言最合理者統(tǒng)一使用。在沒有更佳選擇的情況下,我在這篇文章中暫且使用目前國內(nèi)較多見的中譯“全球在地化”。
在英語文獻中,“glocalisation”一詞首先出現(xiàn)于工商界,原指跨國生產(chǎn)或在全球市場銷售的商品為適應(yīng)各地的生產(chǎn)和消費的傳統(tǒng)與習慣而對產(chǎn)、銷以及產(chǎn)品本身都做了調(diào)整、兼顧了全球與當?shù)仉p方或多方的需求這樣一種現(xiàn)象。這一術(shù)語在2000年前后被歐美人類學界借用[29],在概念、范疇和運用上都比經(jīng)濟學中的原意大有擴展。但在國外的音樂研究著述中,明確地使用這一術(shù)語并以此為中心議題的文論卻至今仍然多見于流行音樂和商品音樂領(lǐng)域,而涉及傳統(tǒng)和民俗音樂文化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我自己從20世紀末開始把研究的重心轉(zhuǎn)移到中國民俗音樂文化中的雜合以及全球在地化現(xiàn)象,曾經(jīng)以此為中心論題對海南、福州等地的民俗音樂文化進行過研討[30][31][32]。
觀照國內(nèi)各界中文著述的情況,雖然于20世紀末已可見到對于全球化與地方化的討論,但明確使用“glocalisation”這一概念及中譯術(shù)語者僅始于2000年[33][34]。此后述介或研討這一論題的中文文章逐漸增多,但卻多見于社會科學界以外的領(lǐng)域例如經(jīng)濟學界或建筑界,在人類學界與音樂(人類)學界則是至今未見,而僅見的以此術(shù)語及概念對音樂現(xiàn)象進行的研討,卻出現(xiàn)在傳播學界,討論的對象是當前流行音樂[35][36]。不過,國內(nèi)音樂(人類)學界有兩位學者的近著與全球在地化概念直接相關(guān),值得注意。楊民康立足于實地考察,先后于2001年[37]和2003年[38指出了國內(nèi)民俗音樂活動中的“全球化與本土化對峙”的現(xiàn)象,又在2008年通過云南一些族群中的基督教儀式音樂活動實例進一步研討了“后現(xiàn)代語境”中音樂文化的“本土化與現(xiàn)代化”的“整合”與“適融”現(xiàn)象[39]。宋瑾通過對普遍現(xiàn)象的整體理性思辨,于2006年提出音樂文化的“中性化”概念并進行了理論探討[40]。這兩位學者并未使用“全球在地化”之類外來術(shù)語,而是各自使用了他們自己的詞語來描述或界定相關(guān)現(xiàn)象。雖然他們的界定與見解跟國外當前的文化雜合及全球在地化概念及理論不完全相同,而且宋瑾文中的某些內(nèi)容我也覺得可以商榷,但他們所注意到的現(xiàn)象和探討的議題卻跟國際學術(shù)界當下的全球在地化論題屬于同一類型。在國內(nèi)音樂(人類)學界中,像這樣敏銳地注意到當前社會文化動態(tài)、與國際學界同步探討最新理論議題且有獨立見解的著述還比較少見。
三、福州游神樂舞:從一種實例思考諸種論題
國內(nèi)的一些學生曾對我說,苦于找不到適合研討當代論題的民俗音樂實例。現(xiàn)在我就從中國民俗音樂中舉出一種實例來說明它與上述各種論題的關(guān)系。這一實例是我長期考察研究的福州民間宗教活動“游神”中的音樂舞蹈表演。我試圖說明,哪怕僅僅通過一種實例,我們也可以緊密結(jié)合并深入討論上一節(jié)談到的所有論題。只要你保持敏銳的學術(shù)思維和眼光并且考察深入細致,你就會發(fā)現(xiàn),可供研討的實例比比皆是,你甚至不必為此遠道跋涉去偏遠他鄉(xiāng)考察,就在你生活的城市或鄉(xiāng)村里,就在你自己熟悉甚至參與其中的當?shù)孛袼字校伎赡馨l(fā)現(xiàn)許多現(xiàn)成的實例可用。正如我這福州游神樂舞考察,我是福州人,我這考察正是當代人類學的“doing fieldwork at home”(在家鄉(xiāng)做實地考察),考察對象就是我從小熟悉的、身在其中的民俗文化。
福州本地的原生傳統(tǒng)宗教是多神信仰而非佛教或道教。本地多神信仰的神詆很多,游神是以敬神謝神祈福為目的的宗教游行,所敬所游的就是本地多神信仰中供奉的神祇。這是草根性極強的本地大眾化宗教習俗,是某一鄉(xiāng)鎮(zhèn)整個父系宗族所屬各村都參與的大型社區(qū)活動,通常一年一度,由宗祠屬內(nèi)的村莊或社區(qū)共同集資舉辦,在春節(jié)、元宵之類的傳統(tǒng)節(jié)日或是擇一吉日進行,各鄉(xiāng)各族舉辦日期不一定相同。游神期間得請戲班演戲娛神酬神,游神本身則絕對少不了音樂舞蹈表演,演藝隊多者可達二三十隊,屬下鄉(xiāng)村較多的大族,游行甚至需時一整天。以下我就把前一節(jié)說過的每一類論題都跟福州游神樂舞結(jié)合加以討論,為使論述明晰,也按照前一節(jié)9類論題的順序排列。但限于篇幅,對于每一論題我只能簡略提示一下研討的方向,至于更具體的詳盡考察報告與研究,則待另文發(fā)表。
1.族群、族群性、身份認同、國家主義、跨國主義
作為宗族活動,福州游神所具有的族群意義不言而喻,是游神活動所彰顯的最突出論題之一。拋開表面上的宗教目的和涵義,游神的深層社會功能和意義之一是一方面增強族群成員的宗族身份認同和宗族歸屬感,另一方面增強整個宗族的社區(qū)凝聚力,進而增強整個宗族在社會整體中的地位和影響力。音樂表演作為游神的重要內(nèi)容,在游神的族群論題研討中也就大有文章可做。音樂表演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何扮演、如何起作用、它跟其他社會角色之間的聯(lián)系等,就都可以成為我們考察和研討的內(nèi)容。鑒于福州游神及其樂舞所具有的這些族群意義,游神樂舞跟族群性、身份認同等議題的關(guān)聯(lián)自然也顯而易見。
福州游神樂舞跟國家主義論題的關(guān)聯(lián)不甚直接,但在一位美國同行最近的一篇論文中我卻發(fā)現(xiàn)了它跟跨國主義論題的關(guān)聯(lián)。該論文報道并討論了紐約東百老匯4家福州人開的“flower shops”(花店)為紐約福州人社區(qū)婚喪喜慶活動提供福州民俗儀式樂舞服務(wù)的情況,著重于討論傳統(tǒng)與全球化的論題[41],而我卻覺得該文報道的情況其實也可借以討論福州民俗儀式音樂的跨國主義論題。在福州本地,受雇為游神、出殯等民俗儀式服務(wù)的民間樂舞班子很多是靠城鎮(zhèn)街頭常見的專營喪葬用品的花圈店做中介,但是也有不少樂舞班子不依靠花圈店而自攬生意。然而不論何種情況,這些樂舞班子都不把自身形象定格在僅為喪葬服務(wù)上,而是婚喪喜慶全都服務(wù)。不少班子更是打出婚喪喜慶從儀式主持到內(nèi)容安排、從司儀到樂舞、全套“一條龍”服務(wù)的廣告。福州民間的此類樂舞班子及其“一條龍”服務(wù),居然在近幾年經(jīng)營到了紐約,可以說是福州民俗儀式樂舞及其文化經(jīng)營在全球化趨勢中的跨國主義表現(xiàn)。跟經(jīng)濟跨國主義現(xiàn)象相似,在紐約出現(xiàn)的福州民俗儀式樂舞及其經(jīng)營,已經(jīng)根據(jù)紐約當?shù)氐那闆r在經(jīng)營方式、服務(wù)內(nèi)容與表演形式等方面都作了適當調(diào)整。紐約的這幾家福州“花店”不但提供從策劃、儀式安排、司儀直至樂舞表演的全套“一條龍”服務(wù),而且經(jīng)營婚喪喜慶一應(yīng)用品及道具(例如花轎)的租售;店名也不再是福州本地習慣上的“花圈店”(wreath shop),那會令人一聽即以為只是喪葬用品店,而是以婚喪喜慶皆宜的“花店”為名,既符合當代中國人的吉慶心理,又適合西方人的審美習慣;在儀式和樂舞的形式和內(nèi)容上,則正因為身處西方,所以更加強調(diào)了福州本地的老傳統(tǒng)而減少了西方形式的表演,例如不再有當今福州常見的西洋軍樂軍鼓隊而著重于嗩吶鑼鼓等中國樂器和福州本地民間曲調(diào)的演奏以及中國傳統(tǒng)式的舞蹈,更加符合紐約福州人的戀故心態(tài)和紐約本地人的觀賞興趣。
2.人口遷徙、離散
上述福州民俗樂舞在紐約的情況,其實還可以用來作為音樂文化離散論題研討的實例。而在中國國內(nèi),福州游神樂舞則可作為實例來討論國內(nèi)人口遷徙的論題。例如在2004年初,福州游神的音樂表演中有一個打著本地“樹嶺村嗩吶班”名號的民間嗩吶班子相當受歡迎,但該樂班演奏的主打曲目卻不是福州本地曲調(diào)而是東北二人轉(zhuǎn)曲牌,其演奏的技巧和風格都十分嫻熟而地道,原汁原味。根據(jù)我對福州本地民間演藝班子的了解,這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本地人雖然通過電視、DVD等媒介看過東北二人轉(zhuǎn),但本地的民間樂手卻不可能把二人轉(zhuǎn)曲牌演奏得如此地道。后來我通過跟這些嗩吶手的深入訪談,了解到該班的老板雖是本地人,但受雇組成樂班的嗩吶手卻全部來自于安徽宿州農(nóng)村。該地農(nóng)村素有笙管樂演奏傳統(tǒng),各村人人能吹嗩吶且喜攀比樂技。在前一節(jié)談到的農(nóng)民工進城的大潮中,當?shù)卮迕駛円步M成嗩吶班子外出,在全國各地以演奏嗩吶掙錢謀生,主要是在鄉(xiāng)村地區(qū)受雇為婚喪喜慶演出。樹嶺班所雇的這些嗩吶手演奏水平較高,曾在東北待了較長時間,期間為順應(yīng)東北雇主和觀眾的口味而學會了當?shù)氐亩宿D(zhuǎn)音樂且學得風味十足。在東北的演奏掙錢機會雖多,但多在戶外表演。2003年末,由于不習慣東北冬季的酷寒,這些安徽樂手南下到了溫暖的福州,受雇于樹嶺班主,成了一個人口遷徙造成音樂跨地區(qū)交流的生動范例。如此,日后他們再度遷徙或返鄉(xiāng)時,勢必帶走福州本地的民間曲調(diào)。
3.表述、話語、權(quán)勢、邊緣化
音樂是一種表述形式。從宗教角度來說,游神的目的是敬神、酬神、謝神、娛神,游神中的樂舞表演,則是民眾為達到這一目的的表述手段。音樂表述跟這種目的之間的關(guān)系、如何表述、樂舞表演中隱含的象征意義以及社會功能等,就都是可以深入考察研究的課題。
4.科技、媒體、傳播
當代科技與媒體的影響和作用在福州游神的樂舞表演中處處可見。與國內(nèi)其他地區(qū)比較,目前福州城鄉(xiāng)是相當富庶的地區(qū)。自20世紀末以來,錄音機、錄像機、數(shù)碼播放機、電視機、電腦、音像燒錄軟件等在福州城鄉(xiāng)已經(jīng)普及,許多普通家庭都能夠自行錄制音像并制作數(shù)碼光盤,而不論城鄉(xiāng),各處也都有此類專營店或從業(yè)者,專門為民俗活動提供音像攝錄和制作服務(wù)。于是在游神中,數(shù)碼錄音錄像技術(shù)成了最常用的科技手段。另一方面,在儀式和游行中,為了講究排場和面子,固然必須雇請樂隊演奏,但為了熱鬧或氣氛,隨隊行進的車輛安裝高音喇叭大聲播放CD音樂也必不可少。而游神隊伍中以及沿途設(shè)壇夾道拜祭的民眾除了燃放鞭炮焰火之外,很多人還攜帶CD播放機播放音樂助興。社區(qū)和個人都喜歡把游神全過程攝錄下來并制成DVD永久保存、饋贈親友,年輕人還喜歡把一些片段上傳到互聯(lián)網(wǎng)共享。當代科技與媒體更加重要的影響和作用還在于它們是民俗音樂的商業(yè)化、西方化、全球化、雜合化、全球在地化等現(xiàn)象的直接成因之一。由于電腦、互聯(lián)網(wǎng)、電視、DVD等當代科技和媒體在本地的普及,本地民眾才可能接觸到外來音樂并將其吸收到本地民俗音樂實踐中。這些情況都是值得深入研討的。
5.環(huán)境、生態(tài)
關(guān)于福州的多神信仰跟本地自然環(huán)境的聯(lián)系,學界已有相關(guān)著述(例見參考文獻[42])。作為福州游神活動重要組成部分的樂舞表演,也跟環(huán)境和生態(tài)密切相關(guān)。游神本身就包含了祈求神靈保佑、風調(diào)雨順、生態(tài)和諧、五谷豐登的重要內(nèi)容和目的,游神中的樂舞表演就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之一。例如,福州游神中有一種傳統(tǒng)舞蹈“八將舞”,是以樂舞形式表述的瘟神崇拜,而福州的瘟神崇拜,則與本地歷史上的自然和社會生態(tài)直接相關(guān)(例見參考文獻[42]p.81-101)。八將舞僅見于閩臺但彼此有異。福州的八將舞在20世紀中期被禁絕二三十年,世紀末在當?shù)孛癖娮园l(fā)的努力之下始得恢復(fù)。根據(jù)我的調(diào)查,最早恢復(fù)且最接近原貌者是福州蒼山區(qū)城門鎮(zhèn)王村的八將舞隊;我曾于1998年跟福州社科所研究員葉翔對其做過實地考察與現(xiàn)場錄像。福州的八將舞在角色、表演、道具、內(nèi)涵等方面都跟自然與生態(tài)相關(guān)聯(lián)[43]。
6.政治、政策
福州游神在20世紀中期曾被認為是封建迷信活動而遭禁絕,這一情況就可作為政治和政策論題的實例。實際上,國內(nèi)當年盛行的極左意識形態(tài)對宗教活動以及相關(guān)樂舞的影響在福州至少持續(xù)到20世紀末。我在1998年6月考察福州蒼山區(qū)城門鎮(zhèn)王村的游神活動時,當時村民們就對外保密舉辦的具體日期,我因為該村親友的通知才得知是該月27日舉行而能及時前往。當我問村民們保密的原因時,得到的回答是:游神被有關(guān)行政部門視為搞迷信,如果相關(guān)部門知道了具體日期,則會采取停止向該村供電等方式來阻止游神的舉辦。這就是政治和政策介入民俗音樂活動的實例。進入21世紀之后,相關(guān)的意識形態(tài)和政策都寬松很多,各鄉(xiāng)村的游神活動就舉辦得風風火火了,而民間專門為此服務(wù)的樂舞班子不論種類、數(shù)量和質(zhì)量也都比以前大為提高。
7.經(jīng)濟、商業(yè)化、商品化、消費、旅游業(yè)
福州的游神跟經(jīng)濟的密切關(guān)系最明顯地表現(xiàn)在活動的舉辦上,而跟商業(yè)化的關(guān)系則最明顯地表現(xiàn)在樂舞班子的運作中。福州的游神是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舊俗,此后經(jīng)過30年的禁絕,80年代末在民間自發(fā)恢復(fù)至今。據(jù)本地老人的回憶,恢復(fù)后的盛況大大地超過了30年前的規(guī)模。這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本地經(jīng)濟的發(fā)展。以我數(shù)十年來實地考察的長期定點福州長樂金峰港口村為例,該村村民原以務(wù)農(nóng)為主,但80年代之后,全村600余戶,都已經(jīng)基本不務(wù)農(nóng),而以辦廠、辦企業(yè)、經(jīng)商為生,且主要在外省發(fā)展,還有很多人出國發(fā)展。目前村中富有家庭年收入達一千多萬元人民幣,一般家庭年收入也達百萬以上,而年收入幾十萬的家庭在村中則算是“窮人”。這種情況目前在福州農(nóng)村并不罕見。雄厚的經(jīng)濟基礎(chǔ),是支撐耗資巨大的游神、葬禮出殯等類活動的基礎(chǔ)。人們以能掙大錢為榮,互相攀比。宗族和社區(qū)活動,特別是游神之類的宗教活動,都靠村民捐款資助,捐款少者會覺得很失面子。社區(qū)雇來參與游神的樂舞班子少則三五班,多則二三十班。由于這些游神、出殯等民俗活動對樂舞班的市場需求巨大,大量民間樂舞班在本地應(yīng)運而生,形成了民間樂舞班的商業(yè)化。據(jù)福建省管樂協(xié)會秘書長鄭貺提供給我的統(tǒng)計資料,福州在1999年僅民間涌現(xiàn)的這種為游神、出殯服務(wù)的西洋管樂隊就已有數(shù)百隊,而此后數(shù)量一直不減。市場競爭不僅直接影響到樂舞班子的組成、經(jīng)營與運作,也直接影響到它們表演的形式和內(nèi)容。所以,經(jīng)濟與商業(yè)化論題當然可以作為福州游神樂舞研究的重要切入點。
8.社會性別、女性主義、后女性主義、酷兒理論
在福州游神等民俗活動中,數(shù)量最多的樂舞班子當屬女子軍樂隊軍鼓隊。我曾以此作為實例討論過社會性別論題[44]。據(jù)我在20世紀90年代對福州多位高齡老人的調(diào)查,西洋軍樂隊于民國初年就已經(jīng)在本地被用于商店大拍賣或葬禮出殯游行之中,但那時全是男子演奏。不論是根據(jù)本地老人的回憶還是根據(jù)我自20世紀50年代初期至今在福州的親身經(jīng)歷,都證實女子軍樂隊在福州是20世紀90年代才出現(xiàn)的新生事物,而且全部產(chǎn)生于鄉(xiāng)鎮(zhèn)地區(qū),即使在市區(qū)活動的女子軍樂隊也來自鄉(xiāng)間。我曾在本地村鎮(zhèn)對民間女子軍樂隊及村民進行過深入訪談和實地考察,涉及女子軍樂隊的成因、發(fā)展、組織、訓練、表演、經(jīng)營、民眾反應(yīng)等方面。這里只簡略提出幾個跟社會性別研究有關(guān)的議題供大家參考:在福州城鄉(xiāng),這種來自于歐美的樂種在20世紀中期的相對沉寂之后,于90年代開始大幅度興盛,其社會原因是什么?而它復(fù)興之后,很快就變成以女子為主力,這種此前從未出現(xiàn)過的現(xiàn)象的社會成因又是什么?同一時期,福州地區(qū)其他種類的民間樂舞班子也開始以全女性班子為時髦,女子班成了數(shù)量最多的民間樂舞班子,男女混合班數(shù)量為次,而全男性班子則數(shù)量最少,這種現(xiàn)象的社會成因是什么?有何社會意義?這一現(xiàn)象跟社會變革和社會意識形態(tài)有何關(guān)聯(lián)?跟當前女性主義和社會性別思潮及實踐有否或有何關(guān)聯(lián)?
9.雜合、雜合化、地方化、全球化、全球在地化
在福州游神以及其他類型的宗教祭祀和游行例如葬禮出殯中,文化雜合與全球在地化的表現(xiàn)非常突出。這里略舉幾例。上述的本地西洋軍樂隊軍鼓隊大部分是以中西雜合的面貌出現(xiàn)的,例如:在樂隊中加進嗩吶跟西洋管樂同奏;以中國大鈸取代西方大镲;以中國民間傳統(tǒng)的指揮方式取代西方軍樂傳統(tǒng)的指揮方式,即大鈸演奏者走在軍樂隊前頭引領(lǐng)樂隊演奏而不是由一個手持西式樂杖者走在軍樂隊前頭負責指揮;所演奏的曲目都是中國曲目;大約一半或更多的女子軍樂隊軍鼓隊服裝是中國傳統(tǒng)或民間特色服裝,例如旗袍、福建惠安女的特性服飾;等等。反過來,游神隊伍里的中國傳統(tǒng)器樂班子中也經(jīng)常混入西洋樂器比如小號、薩克斯管或者西方當代流行音樂中用的架子鼓;一些本來是由嗩吶領(lǐng)奏的民間祭祀音樂被改成了以西洋小號領(lǐng)奏;游神中傳統(tǒng)上威嚴行進的本地諸神,現(xiàn)在越來越多地隨著西洋軍樂的演奏或者擴音器中播放的當代流行音樂而一路載歌載舞,所跳的舞蹈則是越來越西化、越來越時髦,20世紀八九十年代跳迪斯科(disco),90年代末則出現(xiàn)了搖滾(rock'n' roll),進入21世紀數(shù)年后更出現(xiàn)了街舞或銳舞(rave)。2008年福州長樂沙堤村元宵節(jié)游神中,濟公居然在眾仙姑的街舞陪襯下肩背著地跳起了霹靂舞(breakdance)。自21世紀初以來,本地游神中除了西方化的音樂舞蹈,還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了亞洲、中東與拉丁美洲的音樂舞蹈,例如“阿拉伯肚皮舞”、“墨西哥舞”、“日本舞”、“韓國舞”、“日本鼓隊”、“韓國鼓隊”等。跟本地的西洋軍樂隊軍鼓隊情況類似,這些亞非拉樂舞在福州也都多少不等地摻合了本地或是本國的因素,成為全球在地化的實例。文化雜合以及全球在地化議題中可資探討的方面很多,例如它們的成因、意義、它們跟其他文化現(xiàn)象的關(guān)系等等。我就曾以福州宗教祭祀樂舞現(xiàn)狀為例討論過全球在地化跟商業(yè)化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45];也曾通過福州游神樂舞現(xiàn)狀來證實:傳統(tǒng)跟現(xiàn)代化、西方化和全球化之間的關(guān)系并不如一些學者所相信的那樣是完全對立的,前者在后者的沖擊之下也并非一定消亡,而是經(jīng)常出現(xiàn)二者雜合的全球在地化結(jié)果[32]。
任何文化現(xiàn)象都是一個多面體。福州游神樂舞就是一個實例。以不同的論題對同一文化現(xiàn)象進行探討,正是針對這些不同層面所作的考察研究,有助于我們對這一文化現(xiàn)象的全面闡釋和了解。忽略多種論題的研討,難免盲人摸象之弊;若循舊日思路一味尋求“規(guī)律”,以為一旦發(fā)現(xiàn)并歸納出文化“固有”的“規(guī)律”就能一勞永逸地解釋所有文化現(xiàn)象之現(xiàn)在、推衍其過去、預(yù)見其將來,則可能只是緣木求魚式的一廂情愿。
本文討論的是當代音樂人類學的國際潮流,所結(jié)合的實例則完全是中國音樂實踐和研究。國內(nèi)讀者若欲了解本文述及的國際潮流和論題在國外音樂研究中應(yīng)用的實例,我建議閱讀2006年在美國出版的一部當代音樂人類學讀本[46]。這是一本文集,選收24篇論文,按照音樂人類學界當前的熱門論題分類編排,每篇是一個論題的實例研討。這一讀本涉及的論題跟本文不完全相同,更沒有像本文這樣對這些論題和相關(guān)思潮做出介紹與解說,但卻提供了常見論題的實例研究論文。作為當代音樂人類學研究實例的最新讀本,該書按照當代熱門論題選文及編排的做法,正好印證了我在本文開始時指出的情況:21世紀的音樂人類學已經(jīng)不再是梅里亞姆時代的音樂人類學了,本學科的主導(dǎo)理論范式已經(jīng)轉(zhuǎn)移,考察研究的重心已經(jīng)從尋找音聲本質(zhì)和“規(guī)律”轉(zhuǎn)移到為了深入理解、闡釋音樂文化而進行的各種社會論題的探討上來了。
致謝:感謝星海音樂學院的研究生吳迪提供了我在該院講座的全錄音,趙璐提供了講座錄音的摘要記錄文字,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方便。
【參考文獻】
[1]Reyes, Adelaida. What Do Ethnomusicologists Do? An Old Question for a New Century[J]. Ethnomusicology, 2009, 53(1): 1-17.
[2]Ivey, Bill. Ethnomusicology an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usic Scene[J]. Ethnomusicology, 2009, 53(1): 18-31.
[3]楊沐.澄清對當代國際學術(shù)理念的某些誤解——由《對我國音樂文化學研究現(xiàn)狀的初步思考》談起[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6,(1):117-127.
[4]張伯瑜.漫談民族音樂學的學科劃分[J].天津音樂學院學報(天籟),2009,(1):34-96.
[5]Merriam, Alan P.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M]. Blooming 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4.
[6]Rossi, Alice S. ed.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eport of a Delegation Visit February-March 1984[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5.
[7]楊沐.也談“回族民間音樂”[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7,(1):47-56.
[8]楊沐.當代人類學與音樂研究二三題[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7,(6):25-31,38.
[9]Yang Mu. Erotic Musical Activity in Multiethnic China [J]. Ethnomusicology, 1998, 42(2): 199-264.
[10]Yang Mu. On Musical Instruments of the Li People of Hainan [J]. The World of Music, 1997, 39(3): 91-112.
[11]楊沐.性愛音樂活動研究—以海南黎族為實例(上)[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6,(3):71-82.性愛音樂活動研究—以海南黎族為實例(下)[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6,(4):83-91.
[12]Guy, Nancy. Governing the Arts, Governing the State: Peking Opera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aiwan [J]. Ethnomusicology, 1999, 43(3): 508-526.
[13]楊沐.儋州調(diào)聲研究[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3,(4):3-13.
[14]楊沐.后現(xiàn)代理論與音樂研究(上)[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1,(1):3-14.后現(xiàn)代理論與音樂研究(下)[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1,(2):41-51.
[15]楊沐.認識后現(xiàn)代主義[EB/OL].南方網(wǎng)理論頻道:嶺南大講壇·藝術(shù)論壇,(第66期).2009-02-14. http://theory.southcn.com/llzhuanti/lndjt/yslt/content/2009 -02/27/content-4947425.htm
[16]張武宜.流行音樂的傳播及其文化學批判[D].武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00.
[17]殷瑩.大眾文化的復(fù)雜面向——以中國流行音樂為中心的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2007.
[18]Yang Mu. Music Loss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A Comparison of the Li and Hui Peoples [J]. Asian Music, 1996, 27(1): 103-131.
[19]Yang Mu. Academic Ignorance or Political Taboo? Some Issues in China's Study of Its Folk Song Culture[J]. Ethnomusicology, 1994, 38(2): 303-320.
[20]Yang Mu. "on the Hua'er Songs of North- Western China" [J].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1994, 26: 100-116.
[21]Yang Mu. Government Policy and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003, 141: 55-94.
[22]Yang Mu. Ethnomusic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Critical Commentary [J].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003, 35: 1-38.
[23]曹麗娜.唐代民間營利性樂舞的生產(chǎn)與流通[D].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2008.
[24]羅霄笑.中國流行音樂商業(yè)化的萌芽—黎錦暉對流行音樂商業(yè)化的嘗試和貢獻[D].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2005.
[25]李逸歆.臺灣流行音樂營銷策略之研究[D].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2001.
[26]陳春聲.土樓建筑與閩粵文化[EB/OL].南方網(wǎng)理論頻道:嶺南大講壇·藝術(shù)論壇,(第46期).2008-08-30. http://theory.southcn.com/llzhuanti/Indjt/yslt/content/2008-09/10/content-4592571.htm
[27]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官方網(wǎng)站中文版.http://www.ccnt.gov.cn/xxfb/jgsz/zsdw/ysyjy
[28]朱大可.梁祝故事:男同志的情感哀歌[EB/OL].朱大可博客.2005-12-29.http://blog.sina.com.cn/s/blog47147e9e0100001i.html
[29]Eriksen, Thomas Hylland. Small Places, Large Issues [M]. 2nd ed. London: Pluto Press. 2001.302.
[30]Yang Mu. Hybridity as a Source of Innovation in Local Chinese Religion: The Case of Festival in Fujian Province [R]. The 36th World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 Rio de Janeiro. 4-11 July, 2001.
[31]Yang Mu.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of Traditional Music—The Case of Performing Arts in Fuzhou, China[R]. The 37th World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 Fuzhou, China. 4-11 January, 2004.
[32]Yang Mu. Preservation, Modernisation, or Postmodernisation of Tradi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of Musical Performances in Traditional Ceremonies in Fuzhou, China [R]. East Asian Music and Modernit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Asian Pacific Traditional Arts Festival. Ilan, Taiwan. 31 August-2 September, 2006.
[33]孫治本.全球地方化、民族認同與文明沖突[J].臺灣:思與言,2000,38(1):147-184.
[34]章仁彪.“城市化”、“后建設(shè)”、“全球城”——中國城市管理與發(fā)展的“全球-本土化”戰(zhàn)略論綱[J].當代建設(shè)(上海市建設(shè)學報),2000,(6):6-7.
[35]殷瑩.文化全球化的復(fù)雜面向—以中國流行音樂為例[J].上海文化,2007,(3):57-62.
[36]張武宜.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流行音樂產(chǎn)制研究——以李宇春為例[R].北京:中國傳媒大學第二屆全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博士生學術(shù)研討會.2008-04-26.
[37]楊民康.“本土化”和“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南傳佛教音樂[A].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中國傳統(tǒng)音樂學會(合編).中國音樂研究在新世紀的定位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下冊)[C].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1.822-837.
[38]楊民康.論城鄉(xiāng)社會背景中的傣族佛教節(jié)慶“賧坦”儀式音樂[J].中國音樂學,2003,(1):88-101.
[39]楊民康.本土化與現(xiàn)代性:云南少數(shù)民族基督教儀式音樂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40]宋瑾.中性化:后西方化時代的趨勢(引論)——關(guān)于多元音樂文化新樣態(tài)的預(yù)測[J].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2006,(3):45-58.
[41]Wilson, Dale. Fuzhou Flower Shops of East Broadway: 'Heat and Noise' and the Fashioning of New Traditions [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6, 32(2): 291-308.
[42]徐曉望.福建民間信仰源流[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43]葉翔.源于福州的臺灣民間陣頭[A].馬躍征(主編).地緣·根源·家園:閩臺地緣關(guān)系研究文集[C].北京:中國聯(lián)出版社.2008.446-455.
[44]Yang Mu. Bringing on the Girls! —The Case of Feminising Brass Bands in Fujian, China. [R]. Music a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joint conference of the Musicological Society of Australia and the New Zealand Musicological Society. Sydney. 27-30 April, 2000.
[45]Yang Mu. Commercialising Traditions—Case Study of a Taoist Rite in Fuzhou, China[R].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Study Group of Musics in East Asia,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 Shanghai. P. R. China. 20-22 December, 2007.
[46]Post, Jennifer C. ed. Ethnomusicology: a contemporary reader [C]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Grancis Group. 2006.

- 2018年山東財經(jīng)大學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
- 2017年山東財經(jīng)大學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
- 2016年山東財經(jīng)大學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
- 2015年山東財經(jīng)大學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
- 2014年山東財經(jīng)大學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
- 2013年山東財經(jīng)大學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
- 2012年山東財經(jīng)大學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
- 2011年山東財經(jīng)大學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
- 2010年山東財經(jīng)大學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
- 2018年濟南大學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