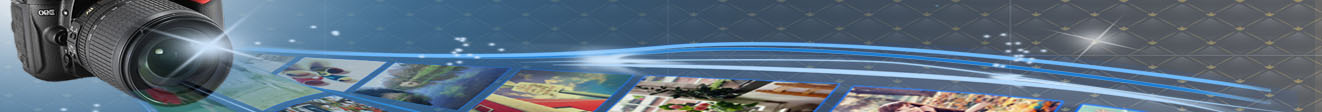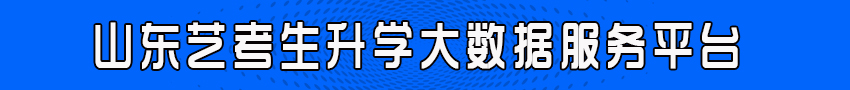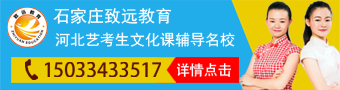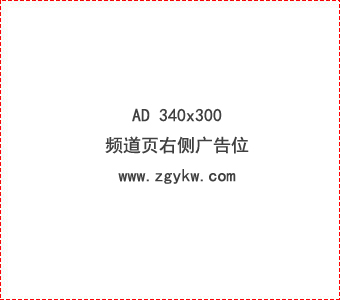“薪傳”舞出血脈情
“薪傳”舞出血脈情
「薪傳」歷久彌新,早已成為跨世代的共同記憶。
它樸實(shí)厚重又浩氣蓋天,強(qiáng)烈的儀式性,隱含林懷民營造島內(nèi)族群命運(yùn)共同體的意念。它的成功,也呼應(yīng)了云門舞集創(chuàng)團(tuán)來以舞蹈投入社會(huì)、歷史及文化的深刻使命。
云門舞集多次來到北演出,給內(nèi)地舞者以極大地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舞結(jié)合的啟示;也給大陸了解臺(tái)灣同胞一極好的機(jī)會(huì)。其實(shí),在「薪傳」中非常集中的表現(xiàn)了“我從哪里來,心向哪里傾”的人文關(guān)懷。因此,當(dāng)舞者以憾人的體力,在古老南音「思想起」的吟詠和朱宗慶打擊樂團(tuán)的鼓聲中,揮灑無悔的青春汗汁,無止境地延展肢體極限。而那條鮮紅的象征著生命正在延續(xù)的“血脈”,從地面升騰成空中舞動(dòng)的火龍時(shí);觀眾經(jīng)過長久屏氣,嚴(yán)肅且殷切注視后,許多人終于不覺濕潤了眼眶。及至謝幕,洶涌漫長的歡呼和擊掌則是表達(dá)著同胞間情感認(rèn)同。
「薪傳」是林懷民在一九七八年創(chuàng)作的作品,也是他第一部作品,是以臺(tái)灣歷史為背景,對(duì)開臺(tái)先民的禮贊。主要內(nèi)容是講了臺(tái)灣祖先去建設(shè)自己家園的開拓史。林懷民說:“「薪傳」血脈賁張;是火的感覺;是商銅的厚重與宋瓷的素雅”。「薪傳」是云門舞集演出場(chǎng)次最多的舞作,二十五年來,已經(jīng)在國內(nèi)外各地演出一百五十五場(chǎng),這次錄象集結(jié)了二十二歲到四十歲的舞者同演。這部作品是云門創(chuàng)團(tuán)五年時(shí)的舞作,林懷民編此舞時(shí)才三十一歲。他說:“這部作品完全看舞者的身體,舞臺(tái)上是臺(tái)灣「力與美」的表現(xiàn)。”
這出舞作堪稱云門舞者的“成年禮”,每一代云門舞者都得經(jīng)過「薪傳」的磨練。
排練「薪傳」是件很苦的事,資深舞者李靜君說:“這是出殺人的舞。跳一次死一次。”林懷民說:“排舞時(shí)隨著舞者動(dòng)起來,在〈渡海〉末段看到臺(tái)灣島時(shí)的場(chǎng)景,還得大聲嘶吼,提振舞者的士氣”。他說:“云門四十年時(shí),我不曉得還有沒有力氣排這支舞,那時(shí)我已六十六歲了。「薪傳」這部作品沒有政治正不正確的問題,而是讓一個(gè)藝術(shù)家找到“回家”的感覺。作品雖然談的是臺(tái)灣移民的故事,但是到了舞臺(tái)上,它是一部有血有肉令人感動(dòng)的作品。”
通過林懷民帶著團(tuán)里人去海邊寫生,體會(huì)肉體與石頭的摩擦?xí)r的疼痛感,在一次次磨練中找到真實(shí)的感覺,外加上本身社會(huì)環(huán)境就處于悲憤和悲壯的情景下。把身體用到極限,挑戰(zhàn)毀滅與死亡的高峰,用一次次堆棧的節(jié)奏處理,使整個(gè)節(jié)目情緒達(dá)到高潮。反映了抵抗外來困難的爆發(fā)力,維護(hù)自己家園。
「薪傳」以閃回的敘述方式,分為八段,分別是:序——唐山、 渡海、 拓荒、 野地的祝福、 死亡與新生、 耕種、 節(jié)慶。
在首演的那天,正好碰到中美斷交,本來要取消這天的演出。但是林懷民堅(jiān)持要演下去。結(jié)果達(dá)到了當(dāng)時(shí)強(qiáng)烈的轟動(dòng)反映,因?yàn)檫@個(gè)作品就是表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臺(tái)灣人民的心,劇情主要表現(xiàn)了臺(tái)灣人靠自己也能生存。
在舞臺(tái)上,演員通過一系列激烈的,碰撞的,身體與外界抵抗的動(dòng)作表現(xiàn)了堅(jiān)強(qiáng)不息的一面。外加舞臺(tái)上設(shè)計(jì)的背景道具極為真實(shí),更把觀眾融入其中,一同感受著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背景下的痛苦與不言敗的頑強(qiáng)精神。
當(dāng)歷史過去時(shí),「薪傳」留下給人們的是身體以外壓力抗?fàn)幍闹w美學(xué)。
我更關(guān)住的到是,從表演中破解那些優(yōu)秀演員們的平時(shí)訓(xùn)練(如何將西方的現(xiàn)代舞蹈技術(shù)與東方古老元素的結(jié)合、傳統(tǒng)的元素如何表現(xiàn)現(xiàn)代人的思想等)。他們的出色表現(xiàn)也絕對(duì)離不開平時(shí)的基本功訓(xùn)練。云門舞者的訓(xùn)練包括現(xiàn)代舞,芭蕾,京劇動(dòng)作,太極導(dǎo)引,靜坐與拳術(shù)。在「薪傳」的排練階段,他們把瑪莎格蘭姆的收縮/伸展動(dòng)作體系和中國戲曲里的毯子功融合在一起,外加又注入了一些閩粵浙地方的民族舞蹈的訓(xùn)練,導(dǎo)致肌肉素質(zhì)都很強(qiáng)。極為吸引觀眾眼球,這個(gè)功勞要?dú)w功于編導(dǎo)林懷民。
說到林懷民,他可真是個(gè)很少見的人才,他原是政大新聞系畢業(yè)的,二十二歲就出了書叫《蟬》,在留美期間一面攻讀碩士學(xué)位,一面學(xué)習(xí)研究現(xiàn)代舞。
1972年,自美國艾荷華大學(xué)英文系小說創(chuàng)作班畢業(yè),獲藝術(shù)碩士學(xué)位。
1973年,林懷民創(chuàng)建了「云門舞集」舞團(tuán),帶動(dòng)了臺(tái)灣現(xiàn)代表演藝術(shù)的發(fā)展。
1983年,他應(yīng)邀創(chuàng)辦臺(tái)灣國立藝術(shù)學(xué)院舞蹈系,并出任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現(xiàn)為舞蹈系研究所副教授。
通過「薪傳」讓人們意想不到的是臺(tái)灣在上個(gè)世紀(jì)七十年代就已經(jīng)有這么個(gè)優(yōu)秀作品,而當(dāng)時(shí)的中國才開始改革,大量的舞蹈還在待著被引進(jìn)。和臺(tái)灣比起來,真是拉下了一大截。
還好的是,我國舞蹈事業(yè)發(fā)展的還真是不錯(cuò),舞蹈上的人才也多了,學(xué)習(xí)的人也多了,還有許多人在世界上拿過獎(jiǎng),為國家爭光過呢。相信未來中國舞蹈的發(fā)展能更記輝煌,期待著那天的到來!

相關(guān)推薦:
- [學(xué)術(shù)論文]戲曲舞蹈的演變與審美特征
- [學(xué)術(shù)論文]中國民間舞元素化教學(xué)的探討
- [學(xué)術(shù)論文]舞蹈感覺形成與發(fā)展的影響因素分析
- [學(xué)術(shù)論文]舞蹈教師素養(yǎng)提升方法
- [學(xué)術(shù)論文]中國古典舞蹈藝術(shù)的現(xiàn)狀和未來
- [學(xué)術(shù)論文]廣場(chǎng)舞在農(nóng)村的發(fā)展制約和對(duì)策
- [學(xué)術(shù)論文]哈尼族铓鼓舞的文化內(nèi)涵和傳承發(fā)展
- [學(xué)術(shù)論文]各類舞蹈呼吸的特點(diǎn)與運(yùn)用
舞蹈
最新資訊
- 2018年山東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
- 2017年山東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
- 2016年山東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
- 2015年山東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
- 2014年山東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
- 2013年山東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
- 2012年山東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
- 2011年山東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
- 2010年山東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
- 2018年濟(jì)南大學(xué)藝術(shù)類專業(yè)招生簡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