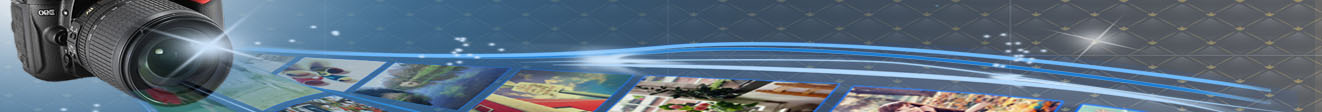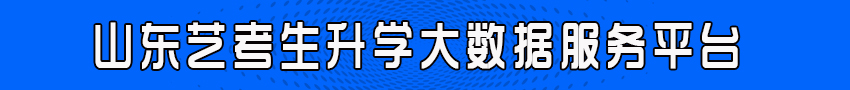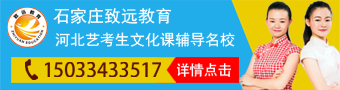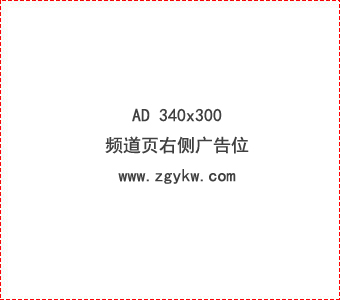簡析消費藝術語境下解讀劇場民間歌舞
簡析消費藝術語境下解讀劇場民間歌舞
無論是“原生態”歌舞《云南映像》還是近日上演的大型原創歌舞集《香格里拉記憶》,對于這些經過舞臺藝術化編排的少數民族民間歌舞,在種種成功的光環及嚴肅的學術爭議背后,值得我們深思的是今日的少數民族民間歌舞究竟發生了何種改變,這種轉變又具有哪種特性和形式。本文從流行消費藝術的角度出發,以大型原創歌舞集《香格里拉記憶》為例,試析今日少數民族民間民俗歌舞所發生的特殊轉變。
一、作為消費品的民間歌舞
(一)消費藝術的民間歌舞
當代法國著名思想家居伊·恩斯特·德波(Guy Ernest Debord) 在其著作《景觀社會》中指出:“在今天資本主義的抽象系統中,比實際的使用價值更重要的是它華麗的外觀和展示性景觀的存在”。其實不管是在西方社會還是在東方社會,在全球一體化的國際語境下,這種大眾對消費品的認識觀念是相同的。現今人們在觀看作為消費藝術品存在的劇場化民間歌舞時,與其說是在感受傳統的民間歌舞文化,不如說是體驗和印證自己心中對少數民族文化的獵奇心理,同時在舞臺的華麗空間氛圍中尋求視聽的刺激,最終滿足于商品消費的心理暗示。畢竟一場花費上百元甚至是上千元的劇場民間舞蹈演出所象征的不僅僅是傳統民間文化的價值,而是高等或者是精英層面的消費文化。這些都是作為消費商品的劇場民間民俗歌舞所暗含的深層意義。
以近日上演的大型原創民間歌舞集《香格里拉記憶》為例,不難看出其作為流行消費藝術商品的特性。劇目上演前期,各種形式的廣告就迅速登陸大眾傳媒的空間;商業中心的巨幅廣告、車身廣告、燈箱廣告、網絡宣傳,最大程度地對大眾傳播演出訊息,使得大眾在無法避免的語境下被動到接受暗示。充分體現了廣告對于流行消費商品的強大功能。除卻劇目打出的近年來最為流行和時尚的“原生態”民間歌舞的標語外,劇目的宣傳詞來自于主題歌《夢會開花的地方》的歌詞:“這里是一塊凈土,這里的空氣清新,這里的天是藍的……這里的青草會跳舞,如果你愿意在地上匍匐凝視;這里的石頭會唱歌,如果你愿意用靈魂傾聽;這里會讓夢開花,這里是夢會開花的地方”在不到百字的內容里,極度地暗示著對人們或主流演出市場對此類表演的審美需求,讓大眾即刻聯想到少數民族文化或直接說“異文化”所象征的新奇與符號化的表演場景。
當你步入劇場,正襟危坐觀看演出,整個劇場從座位、舞臺燈光背景到演員服飾,都按照觀看的最佳效果進行了恰當的調整,甚至歌舞表演的歌唱曲調、舞蹈表演的動作套路和起勢也都為了舞臺表演的特殊性作出了重大的調整。所以,當我們在舞臺上看到所謂的“原生態”民間歌舞表演時,其中對少數民族傳統民間歌舞儀式的舞臺再現,都是脫離原本生態人文環境的移風異俗的動態展演,失去了民間歌舞原本所具有宗教、民俗儀式性的文化內涵。《香格里拉記憶》第一幕《朝圣》中,化身藏民的舞蹈演員叩著等身長頭、點著酥油燈、轉著經幡柱、同時還轉著轉經筒,試圖還原一個真實的藏傳佛教理佛朝圣的儀式過程,但是我們看到的卻僅僅是一個刻意營造的華美而新奇的舞臺畫面。因為特定時間和空間的改變,使得一切都那么的不真實。《夢境》中的群僧辯經部分,極盡人頭攢動的喧鬧和聽覺的震撼效果,可是在佛寺中真正的辯經活動又怎會是這般場景呢?
當然這些失去的都是與作為消費品的劇場民間歌舞的表演要求格格不入的,舞臺演出需要的是震撼的效果、華美的表現,傳統民間歌舞中粗糙的動作起勢、有礙觀看角度的隊列都要重新改造。這一系列的加工再創作為的就是滿足觀眾對于作為消費品的劇場民間歌舞的消費需求——強烈而震撼的視聽感受。《香格里拉記憶》第三幕中《踏舞》部分,這個節目也是此劇中表演的高潮之一,男女演員充滿控制力的踢踏跳躍,贏得觀眾無數的掌聲。但是,真正的藏族踢踏舞的律動是向下的,而不是劇中女子領舞所作的向上的律動起勢。呈現出愛爾蘭踢踏舞的律動風格,這樣的改動雖說是增加了舞臺表演的視覺美觀,但是卻是完全的失去了藏族傳統民間踢踏舞的文化內涵。就像網絡宣傳的那樣:“該舞是集東西方文化融合的原創作品,把西方現代舞蹈藝術與藏民本土的真實生活融進一個舞臺,強調了快樂的主題,讓觀眾獲得心靈的愉悅。”作為一場商業演出來說,《香格里拉記憶》具備了完美的成為消費品的條件,可以滿足絕大多數觀眾對它的審美期待和消費需求。畢竟,觀眾走進劇場觀看表演只是為了獲得心靈的愉悅和放松,他們只是把演出當作一種流行的娛樂消費,而不是為了真正的體驗純正的少數民族文化,這也是劇場化少數民族歌舞發生轉變的原因。
(二)社會地位和功能的轉變
自從建國以來,少數民族民間歌舞藝術一直都活躍在舞臺表演的領域。我國各層級的專業歌舞團體都致力于將各個少數民族群體的傳統的少數民族民間或民俗歌舞中的具有文化象征意義的動態“符號”提取出來,以舞臺表演為目的、結合專業的歌舞編創手法,進行對傳統民間歌舞的舞臺劇目形態的打破原有文化形態結構的創作。這種編創的結果,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少數民族民間民俗歌舞的文化內涵及外在形態。專業領域內將這種新形態的少數民間歌舞稱之為“劇場化”形態的民俗歌舞表演。
劇場化的少數民族民俗歌舞是一種現代社會流行的文化娛樂方式或文化消費方式。雖然作為構成現代流行消費藝術的內容之一它一直都存在。但是,少數民族民間歌舞藝術真正的進入“流行”藝術或消費藝術商品的行列,卻是在知名舞蹈家楊麗萍成功推出“原生態”云南少數民族民間歌舞《云南映像》之后。《云南映像》的成功體現的是它作為流行藝術的特性,廣告的宣傳效應、絕對的空間和心理暗示,完整的視聽享受,種種的因素相加完美地演繹了符合消費社會形態下大眾對少數民族民間歌舞的審美期待與需求,使得廣大觀眾或大眾直接或間接地接受了《云南映像》模式。自此,以《云南映像》為標準的劇場化少數民族民俗歌舞步入了主流消費市場,成為了流行藝術消費品。傳統少數民族民間歌舞劇場化的轉變,給傳承千年的各少數民族民俗民間舞帶來了巨大的改變。這種改變的范圍和幅度涵蓋了從文化內容到社會功能,讓少數民族民間民俗歌舞呈現出一種全新的文化內涵。
二、新文化內涵下的轉變
脫離傳統生態文化環境和表演語境的傳統民間歌舞,在劇場舞臺的新的生態文化環境和表演語境下,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劇場形態的表演性民俗民間歌舞。
(一)劇場化轉變的原因
劇場化的民俗歌舞表演,是傳統民間歌舞在消費社會形態下,作為消費物品而存在的表現。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 在其著作《消費社會》中提到“流行藝術是否是我們所談論的這個這種符號和消費邏輯的當代藝術形式,或只是一種模式效應,即它本身是一種純消費物品?……我們可以承認流行藝術在(根據自身邏輯)將自己變成單純物品的同時改變了一個客觀世界。廣告具有相同的曖昧型。”作為流行藝術的劇場化民俗歌舞,在城市文明的快速普及趨勢下,徹底的重新定義了傳統民間歌舞在社會語境下的概念和功能。無論是大型民族舞蹈詩史《東方紅》、楊麗萍出品的“原生態”云南民間歌舞《云南印象》、《云南的響聲》,還是近期問世的大型原創歌舞集《香格里拉記憶》都是現代流行藝術語境下的產物。他們的共同特征為,由專業的舞蹈編導,以劇場表演為目的,主動地將原生態環境下的少數民族民俗民間歌舞中具有典型性的、即成風格的動態律動作為創作的主要題材,以專業的編舞技法對題材進行加工編排,反映特定的內容,最終以消費藝術品的劇場民間民俗歌舞形態投入演出市場。這種改變體現的是在流行文化語境下,作為消費品而存在的少數民族民間歌舞,被賦予的商品性質的文化內涵和劇場表演性的外在形態。
(二)劇場化轉變的形式
從原生態的田野到劇場化的舞臺,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表演語境的轉變,使得少數民族傳統民間民俗歌舞呈現出較傳統原生態的少數民族民間歌舞更明顯的文化內涵和外在形態的轉變。如下對這些轉變作出分析:
1.由自娛到表演。傳統的原生態語境下的民間歌舞以各少數民族民間傳統節日慶典、民俗活動為表演場所,活動中民眾自發參與到其中歡歌樂舞,具有典型的自娛性。劇場性民俗歌舞則一改傳統少數民族民間歌舞的自娛性常態,成為有專業舞蹈演員在劇場舞臺表演給臺下觀眾欣賞的演出節目。《香格里拉記憶》第二幕《青稞酒》中的弦子、鍋莊是傳統的藏族民間歌舞,具有明顯的自娛自樂性質,在傳統原生語境下人們圍著篝火騰躍起舞,沒有觀眾只有集體的參與,共同歡慶和宣泄。隨著時空、表演語境的轉變,《香格里拉記憶》中的弦子、鍋莊早已改變初貌成為一種表演性的民間歌舞。
2.由參與到旁觀。傳統形態的少數民族民間歌舞是民眾親自參與其中的民俗活動,劇場化的民間歌舞則實現了由參與到旁觀的分工。觀眾在劇場觀看由專業舞蹈演員表演的成品少數民族民間歌舞表演劇目。大型原創民間歌舞集《香格里拉記憶》第二幕情景舞蹈《酥油茶》、歌舞《山羊調》在沒有登上舞臺之前,在原生環境中都是民眾親自參與其中的生產活動和民俗活動。舞臺就是一個特定的時空交界點,把參與的演員和觀看的觀眾分隔成兩個區域。
3.由隨機到規范。原生態環境下的少數民族歌舞活動中,無論是歌還是舞其表演的動機和動勢多是自然而隨機的,沒有一個準確的標準。劇場化民間歌舞在表演時則是要按照一定的被規范了的動作標準來進行,要求演員無論人數的多少,都要呈現出整齊劃一或錯落有致的舞臺畫面。舞臺表演的特殊性規定了任何一種非舞臺形態的歌舞都要按照舞臺表演的規定進行制式化、統一化的編排和表演。《香格里拉記憶》中無論是第一幕中的藏背鼓、塔城熱巴鼓,第二幕弦子、鍋莊、各男女雙人舞,第三幕中的踏舞、各種鼓舞,都是按照舞臺表演的要求進行過編排和改動的,對舞蹈時演員的動作起勢、動作節拍和動作幅度都有精準的規定,同時還要保持美觀和優雅。
4.由傳承到編創。傳統的少數民族民間歌舞其傳承的唯一方式就是世世代代的師承關系,而劇場民間民俗歌舞則打破了這種傳承方式。劇場民間歌舞由專業的舞蹈編導自發創作,編創出成品舞蹈及風格性動作,由舞蹈演員在表演的過程中自發學習,并且隨著劇目的持續演出而在舞臺的空間范圍內有效的傳承。并且這種傳承還有著非凡的滲透力,對遠在千里之外的原生地的歌舞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香格里拉記憶》的舞臺表演風格、舞蹈編排手法都屬于《云南映像》的即成模式,同時在各個少數民族聚居地的原生環境中人們也自發的對本民族的傳統歌舞作出源自《云南映像》風格的改動,這種兩個時空的傳承體現的正是由傳承到編創的新傳承關系。
由自娛到表演、由參與到旁觀、由隨機到規范、由傳承到編創四個轉變過程,不僅僅體現的是現代化城市進程中,城市文明對異文明的侵蝕,同時也體現了進入城市作為消費社會流行藝術消費品的傳統少數民族民間民俗歌舞,所體現出的新文化內涵與表演性外在形態。
三、結語
透過對大型少數民族原創歌舞集《香格里拉記憶》的消費藝術品解讀可以看出,當傳統原生態語境下的少數民族民間歌舞成為流行消費藝術品時,它同時就步入流通的演出市場,成為純粹的消費商品,脫離了傳統的文化生態環境,成為了劇場形態的舞臺表演民俗歌舞。這種文化形態上的轉變,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產生的,是少數民族民間歌舞發展進程中的又一個新里程。
參考文獻
[1]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 [M]. 劉成富等譯,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 2008年第3版.
[2]居依 德波.《景觀社會》[M] 王昭鳳譯.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2007年5月第二版
[3]樸永光.《舞蹈文化概論》[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2009年2月第一版 .
[4]幕羽. 破解《藏密》之迷 [J]. 北京:舞蹈雜志社. 2008年1月 .總第317期.
[5]于平.《舞蹈形態學 .[M] .北京. 北京舞蹈學院 .(內部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