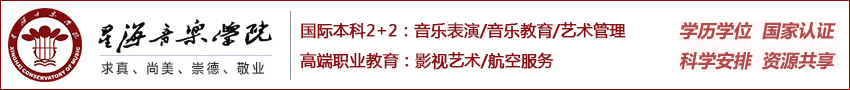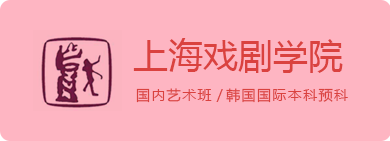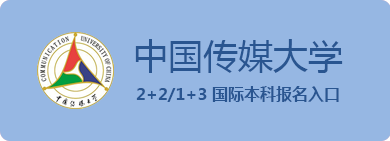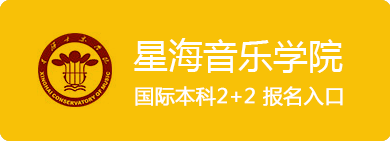音樂表演者表演藝術論文
作者暫時放下了音樂美學的視角,轉從心理學的視角來闡述“情與理”的具體內容及相互關系,如把現實生活中人的感情,稱為藝術心理學中的“一般感情”;論述“感情”時引用了曼德勒的反饋的環路;而在闡述“情緒”這一名詞時,則用了六個心理學的專業術語對其規律性現象進行分類,即:層次性、運動性、復合性、共鳴性、實在性、生物性。這就再一次證明了本章論證的理論性、科學性,可謂是環環相扣。但就這一大段寫作的整體思路來分析,筆者認為有個不妥之處,即作者之前非常清晰地分出了的“感情”、“情感”、“情緒”三類,卻在具體論述時將“感情”與“情緒”的論述層次混在了一起,這就很容易讓讀者產生誤解,即認為“感情”與“情緒”是人類“情”中對等的兩個方面,而實際上作者在之前已經提到“情緒和情感都是同一感情過程的兩個側面”。
在第一段落結尾處,作者并沒有忘記回歸到本章重點的理論視角—音樂表演美學,點出“有識之士關心美育的重要原因”,并引出下一段的內容—音樂作品中的情與理。作為第三段、第四段、第五段的總綱,第二段開始便提出“古典樂派重理,浪漫樂派重情,印象樂派重美,商業藝術重貨幣”的筒言,得出音樂藝術“復雜性從屬于第一性的社會存在”的結論,這是作者結合美學理論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入題的;接下來文中又引用維戈茨基的《藝術心理學》的內容,用以說明“藝術世界不同于現實世界”,即音樂表演藝術中情與理的特殊性,很自然的過渡到了音樂美學領域中的內容—讀譜、練習、舞臺表演三者中的情與理的特征與關系。作者根據表演者進行作品練習的順序將音樂表演時遇到的情與理進行了排序。首先是讀譜過程中的情與理,這段闡述顯現出作者寫作的高明之處—將音樂語言的內容、音樂體裁的內容分別擺出來,從局部論證情與理在讀譜過程中的重要性及相互關系。此處,作者幾乎全是從音樂表演美學的視角展開陳述與論證,如文中首先從樂理的知識點切入,陳述構成音樂作品的幾乎每個小的音樂因素都離不開“情”字,通過這些小的音樂語匯,表演者“可以了解作品的情緒特征”,而音樂表演中的“理”正是“這一系列的情緒特征聯成的一個整體”而“構成了一定的邏輯關系”。
為了使文章的論證更有說服力,緊接著作者就例舉了胡登跳先生的作品《問》,借茅原先生的“筆”來闡述音樂讀譜過程中情與理的關系以及二者的重要性,說道“藝術感情也起著思想的載體的作用”,并得出結論“感覺引起想象,想象引發感情,先體驗了感情,后領悟思想內容。”可見,情是理的前提,理是情的發展的必然趨勢。接下來,作者又強調演奏者創造獨特的個人演奏風格的重要性,而要達到獨特性,就必須在音樂作品中融入表演者獨特的情。文中又以浪漫等樂派的作品特征為例,再次點出情的重要性和部分個性中的共性—民族性。在第四段中,作者順承著第三段的內容展開“練習過程中的情與理”的論述。這一段落,楊易禾先生非常清晰地、很有層次感地將整段內容分為了兩大類進行闡述,即“練習性練習”與“表演性練習”。作者使用了大量的篇幅論證了這樣一個道理—音樂作品中的“理”必須靠前,只有“理”到才能“情”到,即在“練習性練習”中,練習者要注意“理”的把握,在“表演性練習”中,練習者要探索“情”的恰當度。在“練習性練習”中,作者引用了胡應麟先生作品中的文字說明一個道理:野狐與小僧皆不可取。筆者理解為:野狐更不如小僧,即練習者在練習時必須首先把握“理”,“手上功夫真正做得到”,否則就只能成為連“小僧”都不如的“野狐”了。對此,作者也有畫龍點睛之筆—“沒有這種精雕細琢,不可能達到上成的表演藝術”,因此,表演者只是一個“野狐”而已。當音樂作品的“理”被掌握之后,練習者便可以開始對其“情”進行探索了,即“表演性練習”,結合文中前一段文字,便可理解為只有“理”而缺乏“情”的表演者頂多也只是一名“小僧”罷了。在這一小段中,作者著重強調了“練習對情緒的宏觀控制”的重要性,從而引出“理智”之“理”的調控作用,說到練習“情”的最高境界是“未成曲調先有情”的狀態,即“理智”之“理”將“情”放入了“規定情景”之中。這些都說明作者不僅重視表演性練習中“情”的練習,也不忽視”理”在這一過程中的調控作用。這一整段的方法介紹性的闡述手段恰好使文章更具有音樂表演的實踐性。音樂表演藝術的最后一階段便是表演的過程,相對于第三段、第四段來說,此段論證的篇幅較短小,但卻簡潔明朗,其論點在表演過程中的運用不容置疑。
俗語: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臺上”的情與理不僅不可忽視,而且更為重要,“在舞臺表演過程中,演奏者必須充滿激情的進入二度創作”,即“情”在此時的重要性,但緊接著文中又指出“感情泛濫的破壞性,決不低于缺乏激情”,點出“理”控制“情”的必要性,并且引用了戲劇表演藝術中“表現派”與“體驗派”曾有過對立的觀點而最終還是在理論上達到統一的例子,說明在表演過程中“第一自我”(理!與“第二自我”(情)的關系,即“第一自我始終冷靜地在監督著第二自我執行演出計劃”,一語中的,倒出音樂表演過程中情與理的相互關系。最后,作者使用了簡短但概括性較強的語言對本章內容進行了總結,從哲學范疇引出“必然性與偶然性”來類比美學范疇的“情與理”,科學地總結了音樂表演藝術中“情與理”的關系:“在一定條件下,此一方起決定性作用;在另外一定條件下,彼一方起決定性作用,二者具有互補性,而且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換。”并且提出:想要成為一名優秀的表演者,就必須“如實的認識它們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深入研究,在何種情況下,那一方應該處于主導地位的規律性……”在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第五段的部分論證中,筆者認為也有欠妥當之處,即作者的闡述手法似乎給讀者一種錯覺:這四段的內容是平行并列的關系。而細讀本章之后卻發現,文中第一段是從情與理的普遍性展開論述,第二段是從情與理在音樂中的特殊性展開論述,這兩段是共性與個性的關系,而第三段、第四段、第五段的內容卻是并列關系,并且都應該隸屬于第二段。如果將第三段、第四段、第五段全部納入第二段的論述中,文章可能將會更有層次感。

 掃碼關注,實時發布,藝考路上與您一起同行
掃碼關注,實時發布,藝考路上與您一起同行